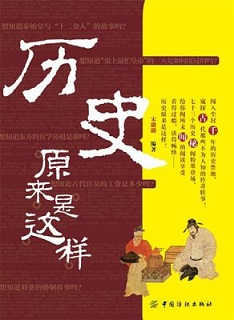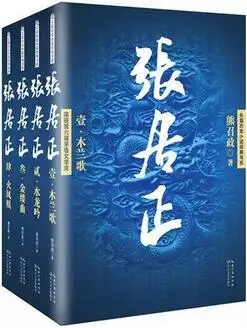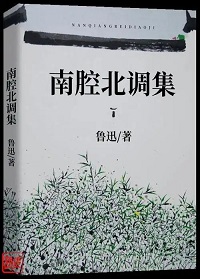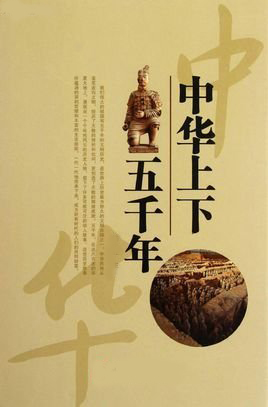十九 工农兵学员
1974年的大学招生推荐指标很快就下来了,我们公社有两个,一个是武汉航空测绘学院,一个是开封师范学院(前身河南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历史系。大老刘书记问我,你想去哪里?我说航空测绘不适合我,开封师院历史系正合我意,学习历史岂不更好?大老刘说,说定了,我马上叫你们支书来,当面拍板。他打了一个电话,不多时支书赶来了。大老刘对支书说,我们三人当面说好,让他上大学去,谁撕毁协议谁是蒋介石!你回去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通过推荐他上大学的决定。
这是我第二次被推荐上大学。等我接到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发来的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是10月中旬了。我立马购得几尺蓝色平纹布,自己剪裁,做了两个新裤头,又购得几尺棕色斜纹布,自己剪裁,让母亲装入棉花,做了一个厚马甲。穿上在守护营时期分发的仿制绿色军大衣,踏上了新的征途。
五言一首
赴开封师范学院途中,过白河铁桥忆旧
1974年10月20日
整装驾长车,征人兴初萧。
笛鸣扰群山,一跃上铁桥。
历历多少事,热血泛狂潮。
致意唤老友,还识旧友否?
三载萌情心,朝夕肝胆照。
当记临别时,男儿泪长抛。
东风已浩荡,又赴万里涛。
但愿共长久,百年永自好。
这是当年的即兴之作,可见心情之大好。当我到校报到之时,我们这一届大班60人已经有59人了,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学员(后来又从焦作矿院转来一人),党支部书记、班长、副班长、团支部书记等班干部均已安排就位。
我和数学系老乡拜会了原本相识的宛籍院党委副书记段某,还拜会了宛籍院团委副书记刘君。
此时,师院“文革”中两个派别的基本力量依然存在。院系负责人除了院级正职是外派来的,其余职务均由原“八二四”骨干担任,而反“八二四”的人则为在野派。
未几,我被院团委任命为团委委员。
在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是我的意外之喜。自幼嗜书如命的我,一头扎进了书堆里。这是入校后不久的一首读书心得:
读《史记·项羽本纪》
1974年11月
初师江东正气激,军霸时节已露否。
滥权自愎悖世道,拔山盖世枉为稀。
虞兮骓兮斑斑泪,垓下乌江幽幽泣。
只缘恨天不知天,直教千古兴豪嘘。
大学教育和管理与基础教育大不相同。教育环境优良自不必说,可管理宽松也不全是优点。上午由任课教师一连讲授4节课,下午和晚上都是自习,全凭个人安排,自我约束。
这种教育和管理正适合我。听了教师几节课,感觉也是照本宣科,缺乏新意。这是很多老师的通病。为了尊重先生,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大教室里,翻看着自己选读的书籍。后来听说中文系一教师古诗词讲得好,便去听了一节。他讲的是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果然与众不同。在三尺讲台上,他非常活跃,且语言干练,深挖教材,警句迭出,讲到动情时,手舞足蹈。我这个自诩熟读《三吏三别》的工农兵学员,也为之深深感动。
开封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阅览室也很大。历史系也有一个很不错的藏书室和阅览室(管理员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老师,据说是师院八大怪之一。他工作一丝不苟,可个人的不良习惯是早上漱口水往脸上一抹就算洗脸了)。这一切良好的设施很适合学生自学。我在那三个学年里,完全是按照初中二年级的自学模式,制订自习计划,除了上午陪着老师在课堂上看书,下午基本上都沉浸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借阅计划中的书籍,晚上则坐在寝室里大书桌一侧(双人桌)读书。
我的第一个自学计划是读伟人传记,读名人传记。马恩列斯毛,无一不读。还要选读他们的著作,易懂的要读,不易懂的也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像天书一样,我偏偏硬着头皮啃了两遍,结果是读懂了一点点——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阶段苦读,使我终生受益。名人传记,不管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我都要读。读鲁迅传,读《鲁迅全集》(1973年版全20卷本)。读了鲁迅写的为数不多的新诗,我就把郭沫若著名的诗集《女神》、《潮汐集》等等都抛到一边去了,只看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自传,看他《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类政论文章。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我自然要看沈雁冰等诸多名家的著作。我还读了拿破仑,读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读了朱可夫元帅的苏联卫国战争回忆录,等等。
我的计划中还有一个是读建国前后所有能借阅的小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暴风骤雨》和《金光大道》这两部名著。这个计划耗费了很长时日。为了“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我在一个时期内,阅读了《荀子》、《韩非子》、商鞅、李斯等不少法家的著作和传记,还试译了龚自珍不少名篇。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本专业,每到期末的一段时间,为了考一个不错的成绩,就专心致志地读一遍授课教师的讲义,兼读《史记》和断代史中那些开国君主的“本纪”之类的史书。
我这个自学习惯一直延续很久,后来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写一部探源历史文学《晋阳英烈》,闲暇时,专门跑到第一师范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借阅《全唐诗》,长达数月,边读边抄写一些重要的诗句。
那时候的高等教育完全落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教育方针,不但将学制缩短为三年,而且还实行“开门办学”,实现了工农兵学员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的教育目的,开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新校风、新学风。
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1975年春),我们历史系74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到了洛阳城南安乐窝村,搞了三个月的“开门办学”。
自入开封师院始,我便进入了“后八二四”时代。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李某林,虽是宛城籍老乡,却是一位骑墙派的大滑头。此人身材不高,常常将背头梳得溜光,说起话来总是一口不京不土阴阳怪气的腔调。他对我拉拢不成,便视我为仇寇,借这次开门办学之机,颇施手段,向我发难。在一次党团员会议上,他含沙射影地警告我和一些同学的接触是“非组织活动”。我毫不客气,反唇相讥。他组织班里同学孤立我,我便团结部分同学,奋起反击。这样,班内同学被分裂成了两派。回校后,李某虽然被调离本系,可那种不和谐的同学关系却一直持续下去了。谭同学对此不解,颇为苦闷,我曾以诗赠之。
赠学友谭君
1976年1月8日
盛夏时节餐蚊多,华日之初晨雾薄。
最苦人生视力短,莫道寰宇天水阔。
欲得健游下大海,闻鸡舞入中流搏。
劝君多读马列书,应假宝鉴辨六合。
我们“74级”第二次“开门办学”是在1975年秋,我带着一个组到了平顶山煤矿七矿。
这时候,“72级”工农兵学员已经毕业了,系里学生干部空缺,我这个共产党员便被任命为历史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书记。在大学历史上,这样的兼职现象,恐怕不多见吧!
历史系有一位在史学界关于“一桃杀三士”的学术争论中,敢与郭沫若对着干的谢作寅教授,教我们“活页文选”。他见我总是特别客气,点头哈腰,还口称“老张”。我这个弟子很是不好意思,总以鞠躬作答。据说老人家在1978年成为省政协委员后,到郑州参加会议因没人车接,又找不到会场而气病交加,不治身亡。
我们在平顶山七矿一个月,下矿井,挖煤,在井下黑手用两个指头掐着肉包子吃,的确和煤矿工人打成了一片。煤矿工人形容他们的工作是“埋了没死,死了不用埋”。这一个月,我们可真是既开了眼界,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随着我们来到七矿的一位讲师胡SY先生,他年近六旬,说话和气,着装邋遢,眼睛近视而不戴眼镜。他抽的烟和我一样,是著名的“前进”牌香烟,点燃一支大约需要五六根火柴。我让他抽烟,他也让我抽烟。我说:“胡老师,你怎么也抽这种烟?”他答:“老婆每月只给我6块钱。”我这才明白,一天一盒烟,一个月可不就需要6元钱嘛。就这位惧内而不起眼的胡先生,不知什么原因,在1978年以后竟然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