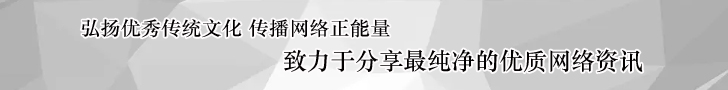(二)
下面是一篇旧作,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不忍舍弃,谨附于此,算是对上半篇的一点补充吧。
人到中年,怀旧思绪日增。夜间睡少,五十年来风雨历程,点点絮絮,魂牵梦绕,欲不思之而不可能。童年玩伴的影子,嘻戏作耍的憨态;少年做事孜孜以求的情愫;青年时期栉风沐雨、上下求索而无悔的执着;步入中年,事业举步维艰终无大成的遗憾;凡数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在脑海里翻来覆去,似趵突泉的气泡按都按不住,不思自现,以至于夜不成寐有许多时。后来我索性拿起笔来,一一记录,聊挽一段情结,亦供闲暇时玩味罢。
公元一九四九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头。当共和国之父毛泽东还在北平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商讨国是的时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生命在宛城东四十多里外名不见经传的村子里降生了,那就是我。犹如原野上亦或是田间路旁一棵出土的嫩草,无声无息,就是在这个已经有了多个子嗣的家庭里,我的到来,也不会引起多大的惊喜。
那时的我,不可能知道已经拥有了一个悠久而庞大的祖国,更不会知道在我的面前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有许许多多情愿和不情愿的事情要做。因为,在我那个生存空间内,人不过数百,方圆不过一公里许,在六岁以前,还从未走出过这个范围。
我的故乡,一个也许并不古老的偏僻村庄。他那久远的历史,已经无据可靠。据先辈留下来的传说以及有限的文字(灼德碑等)记载,经我考证,从始祖张伟(音)始,到现在的子孙,仅历十代,数得过来的历史也不过一百九十年上下。
村上除了赵、宋、吕、王少数外姓人和几家同姓不同宗的原住民以外,其他人口全属于这个弓长氏大家族。如果编写村史的话,可以说就是一部以这个家族为主线的历史。在近二百年里,虽然有伟公父子六人创下的显赫的业绩,可在他们的后人中,却也出现了像荣庆等震慑于百里之外的大杆子头,出现了赤巴脚双手打枪、百步穿杨,在国民党监狱中几进几出的黑道上的传奇人物。除他们之外,人老几代基本上还是无声无息的,自种自吃,自生自灭。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被人吃下了,又拉下了,谁也不会记得起他们。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甚至于连他们的名字在后代子孙中都没有留下来。
农谚有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是苦人生之短暂也。人寿不过百年,不管是贵如王侯,抑或是贱如平民,春光有几?炎夏有几?秋风一起,便叶黄枝枯,要做一番交代了。难怪连踌躇满志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兼著名诗人的魏武帝曹操也不得不浩叹“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
纵观人生数十年,最美好的时光无过于在母腹中的十个月。那时光景一如乐山之卧佛,无苦无愁,无忧无虑,无惊无险。兴之所至,伸伸懒腰,施展一下拳脚,也不会惹出任何麻烦,反而会赢得父母的一番爱抚。倘若一出母腹,便有千般苦楚万般灾难在等候着,便是帝王是总统亦不例外。当然,人生也有不少欢乐,但所要经历的更多的则是不知有几番风雨,几多凄苦。
人生之苦,非吾今日立论。无论古今中外,哲人早有定评。源自天竺的佛学也承认,生老病死,皆是痛苦。基督教《旧约全书》更是把它解释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神便罚他们及其子孙终生受苦。所以,大家都看破了这个世界,谁都不情愿步入红尘,甘愿永远躺在母亲那温馨惬意的摇篮中。我这个说法,诸君也许不信。大凡观察过新生儿出世经历的人,便知此言不谬。人之出世也,一脚踏出母腹,无不愁眉苦脸,满脸都是皱褶,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你若问其原因,回答你的至多不过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
我既然不情愿来到这个世界,就消极而被动地对待周围的一切人一切事物。这个宗旨以致于成为我终生的处世哲学。这一来可苦了父母,从出生那一刻一直到三岁,不怎么哭,也不怎么闹,一天到晚,不吭不哈,甚至连身外的事物,忙忙碌碌的人物,也不愿多看上一眼,只静静地躺在简陋而破旧的床上,躺在父母亲的怀里,或者是在平民人家才有蒲团上静坐半日。起初,邻人都以为我是个傻子,父母虽然溺爱地戏称我伈子(伈,惧貌,宛东方言称为伈子,即傻子),可他们也着实有点担心。
二十年后,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强壮的汉子。在家乡人的眼里,这个曾经在“文革”中充当过红卫兵头头的中学生,曾经在焦枝铁路上修筑过铁路、扛过枪、吃过“皇粮”的公家人,几经沉浮又踏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大学生有出息了。在流露出称许、羡慕的目光的同时,他们又不时地拿我小时候的怪模怪样说笑一番。六祖母曾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对母亲絮叨:“娃儿小时候像一尊小泥人似的粘在蒲团上,你不喂他,再饿也不说饿。喂他就吃,不喂他,一声也不吭,呆怪着脸,谁也不看。”
据母亲说,那时的我人小脾气大,喂饭时热一点凉一点早一点晚一点,马上就怪了,沉着个脸,一股气不吭。母亲只好哄过来劝过去,我才再把嘴张开。这种把话藏在心里不情愿表露、爱静而不爱动、不喜不闹也不求不争的与生俱来的怪模样,大概与我后来不以富贵而欢喜、不以贫贱而耻之、坦坦荡荡、甘于淡泊的心志,是一以贯之吧。
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且不算以后的十几个年头,母爱的付出究竟有多少?恐怕连现代的电子计算器也是无法算清楚了!唐代那位一生穷困潦倒的大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正是对伟大母爱的歌颂。以后多少年里,奔波在外的我,很少有机会在双亲身边尽孝,无法报答父母的恩情。深深的内疚,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我的心。没想到母亲晚年竟患了中风之疾,卧床不起,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我在单位请了假,昼夜护理在病房里,出院后又延医到家诊治,还携母到外地寻访名医针灸,一连四年,喂药喂饭,洗手洗脚,穿衣戴帽。一有闲暇,还用绳带吊着母亲右脚,像提偶戏里的样子,提着老人家的右脚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以期锻炼恢复。这才使我这棵区区小草,以报三春晖于万一。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给我过多的机会,在第四个年头上,竟然意外地走了,结束了她那艰辛而伟大的一生。在以后很多年里,我每思及此,无不悔恨不已,忍不住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