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而不诬,信而不盲从:历史认知的辩证之道
繁体在信息爆炸的当下,“西方伪史论”以全盘否定古希腊、古埃及等文明真实性的姿态持续发酵,既引发了对历史真实性的广泛讨论,也暴露出认知层面的极端倾向。历史作为人类对过往的记录与解读,确实存在主观建构的成分,中国正史中的“春秋笔法”与历代王朝的正统叙事,早已印证了“史由人书”的局限性。但将这种局限性无限放大为“西方历史全为伪造”的论断,实则走向了另一个认知误区。对待中西方历史,唯有秉持“疑而不诬,信而不盲从”的辩证态度,以科学方法考辨史实,方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质疑精神是历史认知的起点,但真正的质疑应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非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潭。“西方伪史论”的部分观点确实触及了历史研究中的争议点:诸如古希腊在缺乏纸张的条件下,如何传承亚里士多德数百万字的著作;某些西方古代文献缺乏明确纪年,其叙事准确性有待考证。这些疑问本身具有学术探讨价值,正如科学思维所倡导的,没有任何历史叙事应当免于审视。中国史学传统中,清代考据学派通过校勘、辨伪、训诂等方法考订典籍真伪,正是这种质疑精神的体现——从《尚书》伪篇的辨伪到《史记》史实的考订,质疑始终是推动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质疑”与“全盘否定”有着本质区别。“西方伪史论”将个别争议点扩展为对整个西方古代文明的否定,宣称古希腊、古埃及文明为文艺复兴后虚构,金字塔、帕特农神庙是近代伪造,这种论断显然违背了实证原则。考古学的发现早已为西方古代文明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石碑与墓葬遗存、古希腊的陶片铭文与城邦遗址、两河流域的泥板文书与建筑遗迹,构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核心准则是同行评议,而支持“西方伪史论”的观点从未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检验,其论证多依赖“不可证伪”的阴谋论逻辑,而非可验证的实证材料。这种缺乏科学支撑的否定,与“金字塔是外星人造”的荒诞论调并无本质差异。
对待西方历史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应陷入盲目崇信的误区。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对证据的解读,而任何文明的历史叙事都存在主观建构的成分。西方史学界自兰克学派以来倡导“如实直书”,但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确实在历史书写中留下了痕迹——将西方文明塑造为“人类文明唯一缔造者”,矮化其他文明的贡献,这种叙事偏差值得警惕。中国史学界曾在一段时间内对西方史学理论盲目照搬,忽视了不同文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恰恰说明盲从外来叙事与否定外来文明同样危险。
科学的历史认知需要建立在对中西方史学传统的理性反思之上。中西方史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传统史学强调“史以载道”,注重历史的教化功能,二十四史作为官方正史,难免带有王朝正统性的叙事倾向;西方现代史学则注重考据实证,形成了多元记载传统,但也存在过度客观化的局限。两种传统各有优劣,却共同指向了“求真”与“致用”的史学目标。清代考据学的实证方法与西方文本批判理论可以相互借鉴,中国史学的“资治教化”传统与西方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能够形成互补——唯有打破文明对立的思维定式,才能构建更全面的历史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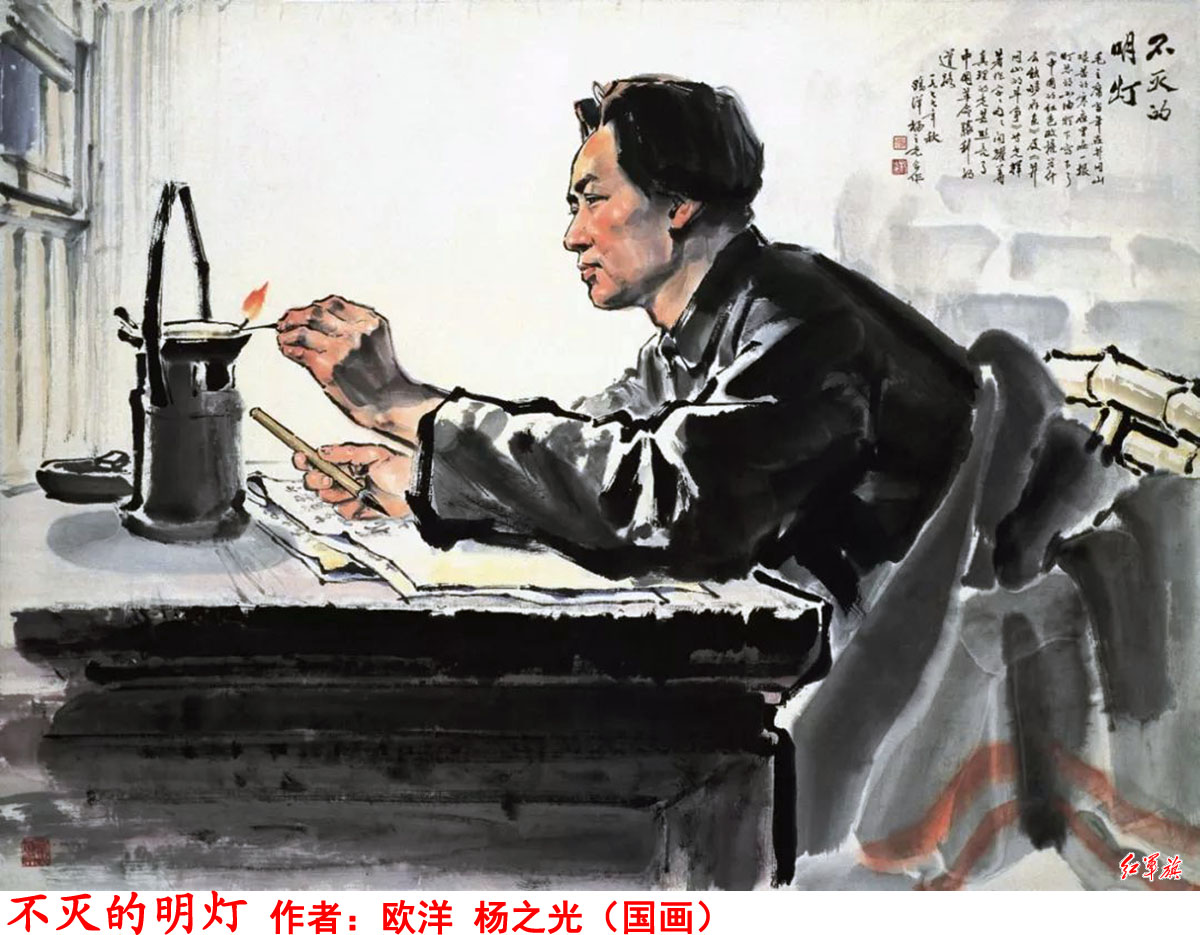
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需要坚守“证据优先”的原则,同时保持开放的认知视野。对于西方历史,应既承认其文明成就的真实性,也审视其历史叙事中的偏差;对于中国历史,既要珍视《史记》《汉书》等典籍的价值,也要正视其中“春秋笔法”带来的叙事局限。正如对待中国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议,学界始终以考古发现为依据逐步推进研究——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到甲骨文的解读,既不轻易否定文献记载,也不盲从传统论断。这种“以实证为依据,以质疑为动力”的态度,同样适用于西方历史研究。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宣泄情绪的工具。“西方伪史论”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对文化自信的误读——试图通过否定他人历史来彰显自身文明优越,实则是一种脆弱的文化心态。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理解与对其他文明的理性认知:既承认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连续传承,也尊重西方古代文明在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的贡献;既批判西方历史叙事中的偏见,也摒弃对自身历史的盲目美化。
历史的长河中,各文明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交融。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共同构成了人类早期的思想高峰,古埃及的建筑技术与中国古代的营造法式展现了不同文明的智慧结晶。对待这些历史遗产,唯有摒弃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以辩证眼光审视争议,以科学方法考辨史实,才能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在批判继承中推动认知进步。这既是史学研究的正道,也是构建理性历史观的必然要求。
来源:万古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