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背后,是被提前透支的未来
繁体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方式早已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悄无声息地重塑了。人们看待一切问题时,几乎都不自觉地带着“价格、利润、竞争、效率”这些资本主义标准来衡量,甚至把市场规律当作某种超越阶级、超越制度的“自然法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从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去分析问题的人,已经极其稀少。
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当经济稍有起色,人们便迅速将其归功于领导的“领导有方”;而一旦经济下行、危机爆发,民众又立刻把怒火指向掌权者,斥责其“无能”“腐败”“胡乱作为”。他们满怀希望地等待新一届领导人上台,期待一场“拨乱反正”,仿佛只要换一个聪明、清廉、有魄力的人,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资本主义下运行的群众,由于缺乏阶级分析能力,于是只能把一切社会变化归因于“领导人”的好坏。他们看到经济增长,就赞扬领导英明;看到下行,就抱怨换个能人。
这是典型的“人治幻想”,而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许多人至今仍相信:“只要有一个清廉、智慧、有魄力的领导,一切都会变好。”
可现实是,只要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内,无论谁上,他们都不得不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
想多发点福利?资本就外逃。
想保护劳动者?股市就暴跌。
想管住资本?媒体、财团、银行体系就全体反扑。
就连“伟大的总统”也不过是华尔街、硅谷和军火集团的代理人。再英明的“领导人”,也无法突破资本主义制度设定的天花板。谁上台,都是资本的奴仆。

美国的现象正是这一逻辑的极端体现。
川普与拜登,两位风格迥异的总统轮番上台,一个高举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大旗,另一个宣扬绿色能源与社会公平。
但无论是谁执政,华尔街的利益始终不受动摇,大型垄断资本依然稳坐钓鱼台;无论是税收政策、基建刺激还是货币放水,最终都无法阻止美国产业空心化、劳动者收入停滞、社会撕裂、债务危机滚雪球般扩大。
所谓的“领导人更替”,不过是给资本统治披上一层不断换色的外衣,而实质没有任何改变。
他们都必须面对同一套制度逻辑:资本的全球配置权力,华尔街的市场意志,巨型垄断企业的游说网络。无论是谁,背后始终站着的是不可动摇的金融寡头与跨国财团。
川普推动制造业回流,最终难敌全球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选择;拜登施行财政刺激与科技补贴,依然无法缓解结构性就业问题与产业空心化。两人各有话语,却无实质区别;争斗表象激烈,实质路径却始终收敛于资本利益的底线。
他们所能左右的,不过是资源的暂时配置与危机的延后节奏,而制度性的分配失衡、周期性的萧条危机、结构性的社会撕裂,始终无法真正改变。
他们不能取消私有制,不能改变利润优先的经济逻辑,更不能颠覆金融资本在国家机器中的主导地位。
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调整螺丝钉的位置,而不是更换这架机器的引擎。他们都不过是被“资本意志”驾驭的执行者,而不是能够改变方向的舵手。
人们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一位领导人身上,其实恰恰证明了群众的思想早已被市场和资本所塑造。
在这种思维模式里,资本主义制度从来是“默认正确”的,不容置疑的,错的只能是“某个坏官”或“某个昏君”。于是人们不是去反思系统本身,而是去赌下一个人会不会“更好”。
这正是资本主义最成功的地方:它不仅通过经济制度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更通过意识形态、舆论、教育和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它让人相信,只要努力拼搏、遵守规则,就能成功致富;
它让人相信,一切社会矛盾都是因为“管理不善”或“技术落后”;
它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的个性、政见、口才、学历上,而不是去追问他们背后的利益结构和阶级立场。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从来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典型的“抛物线”——一旦进入“繁荣期”,看似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但这种繁荣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换来的。它依赖债务、泡沫、环境掠夺、帝国主义输出矛盾来维持表面的增长。
一旦资本积累遭遇瓶颈、市场饱和、金融泡沫破裂,便立刻从高点跌落谷底,爆发危机与萧条。
这样的周期性起伏,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是生产的社会化与所有制的私人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现代资本主义高度依赖信贷与金融工具来拉动增长,本质上是一种大规模的“借未来的钱来消费今天”的模式。政府赤字不断扩张,企业依靠债务维持运营,个人靠信用卡和房贷透支生活。看似流动的资金和高涨的消费,实则是一种延后的崩溃。每一次“增长”的背后,是更深的债务陷阱,而每一个泡沫的破灭,都会波及数代人。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不断压榨劳动力,不仅延长工时、压低工资,还通过外包、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手段,转移风险、削减福利,把劳动者牢牢锁死在“生存焦虑”的链条中。代际之间的上升通道日益堵塞,年轻一代在“内卷”中耗尽精力,中年人则在“负债”与“绩效”之间苦苦挣扎。这种对人力的持续剥削,看似换来了效率,却牺牲了人的尊严、健康与创造力。
资本不仅掠夺本国的资源与劳动力,更通过全球化的方式输出剥削,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监管更薄弱的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核心国家垄断高利润产业链,而边缘国家被困在“血汗工厂”中无法自拔。这种地缘性的掠夺,实际上是对全球剩余价值的集中掠取,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延续形式。
在逐利本能的驱动下,自然被无限度地开采、污染、耗竭,仿佛永远不会反扑。但环境账终将来临:气候异常、极端天气、资源危机、公共健康问题不断加剧。而当这些“生态债”开始反噬时,最先承受苦果的,依旧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
所以,那些“增长曲线”背后所代表的,从来不是什么真正的繁荣,而是一个注定无法长期维系的泡沫结构。当这一结构达到极限,就会迎来剧烈的修正——周期性的萧条、金融危机、就业崩盘、社会动荡接踵而至。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的次贷危机、乃至今天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高利率与失业并存的“滞胀”,都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制度本身必然的内在结果。
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经济运行机制,更在于人们如何理解这一切。
今天的大众,往往把经济周期的涨落归结为“领导人是否有能力”。经济向好,就认为是执政者“治理得当”;经济下行,便指责其“政策失误”、“管理不善”。
这种认知模式看似理性,实则掩盖了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高估了“个体意志”的作用,而忽略了制度运行的必然性?
在资本主义框架中,哪怕是最聪明、最勤奋、最有远见的领导人,也无法跳出资本积累逻辑的天罗地网。他们可以暂时缓解矛盾、推迟危机,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泡沫的生成与破裂,因为整个系统的运转逻辑并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核心,而是以“资本增值”为唯一目标。
制度不是中立的。它有它的服务对象,有它的优先权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增长的优先级永远高于人的全面发展,效率高于公平,利润高于尊严。生产在不断膨胀,但消费能力却被压制,收入分配的失衡注定让“过剩”成为常态。而最终买单的,往往是那些被压在利润表背后的人。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不是人驾驭资本,而是资本驾驭人。”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本质揭示。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商品、市场和投资,更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价值导向与分配体系。它主宰着政策方向、社会结构,乃至人们的情感和欲望。
遗憾的是,今天大多数人仍困在“换领导就会好”的幻觉之中。他们不是愚蠢,而是被剥夺了理解现状的工具。主流话语体系避免谈论阶级、剥削、所有制这些根本问题,把一切矛盾简化为“个别无能”或“局部调整”,使得人们无法识别危机的真正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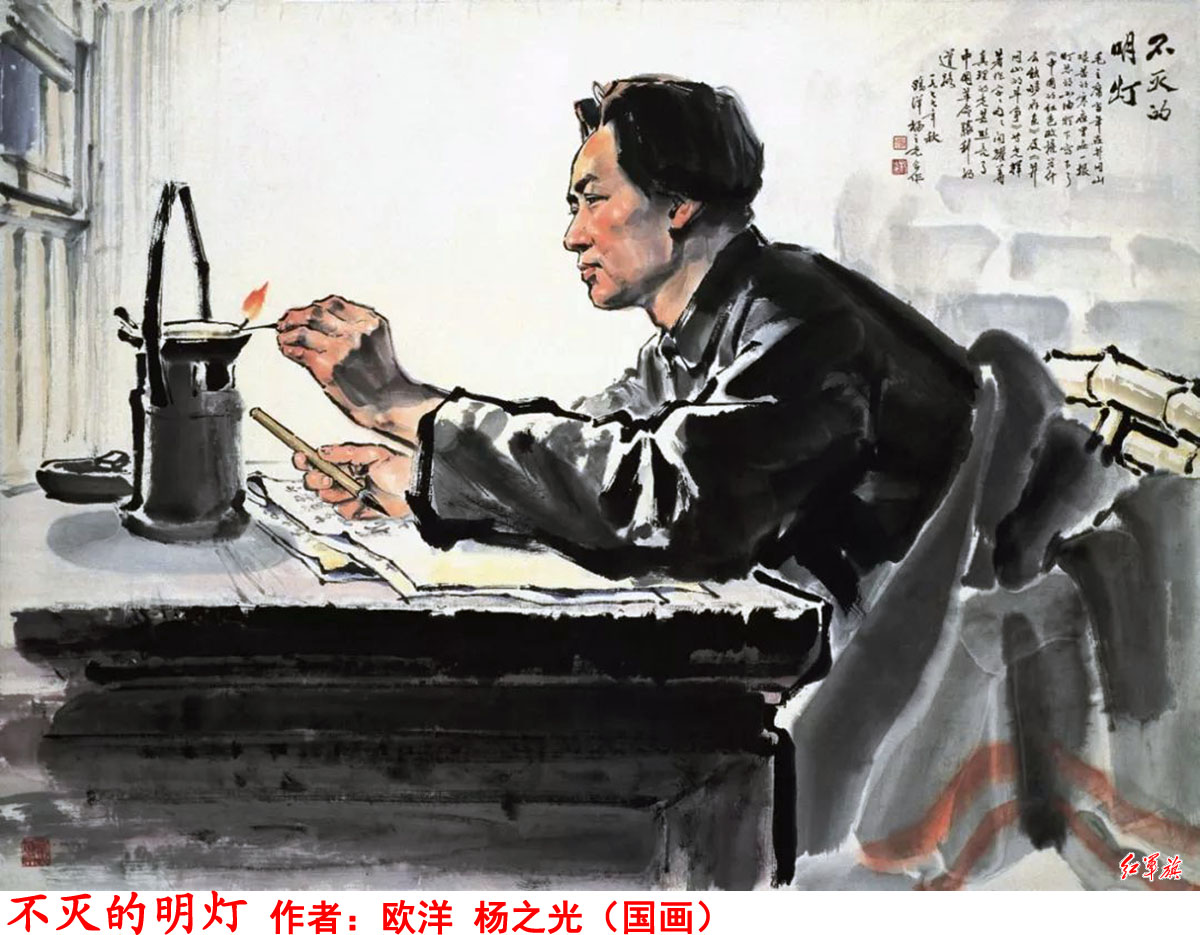
当人们痛苦,却看不清源头,就只能寄希望于“更聪明的天选之人”,或者寄望于自己的“更努力”。而在一次次幻想破灭之后,他们仍会归因于个体,而不是系统;归因于表面现象,而不是深层结构。
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隐秘、也是最成功的控制方式——让你在深陷牢笼时,依然相信牢笼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真正的解药,恐怕不在于继续押注下一位更有魅力的领导,也不在于一次次制度内部的技术性修补。
也许,我们需要换一种方式思考整个社会运行的逻辑,而不仅仅是关注“谁来管理”。
毕竟,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所谓的“繁荣”与“衰退”,一次又一次看到政治人物在“救市”与“托底”中疲于奔命,我们是否该问一句:这个系统本身,是不是出了问题?是否有一种可能,这种以利润为主导、将一切都商品化的机制,在根本上就无法真正保障大多数人的稳定与尊严?
当然,历史的答案并不总是清晰可辨。许多曾被推行过的路径,在今天遭到批判、被否定、被污名、被遗忘;一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方案,也未必完美无缺。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更合理的方向,而只是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探索的早期阶段。
当今的世界越来越复杂,社会的矛盾也越来越难以用“市场调节”四个字轻易化解。在经历了无数轮的兴衰之后,我们或许不该再沉迷于某种“伟人带来奇迹”的叙事,而是去重新理解普通人自身的力量与可能。任何制度,最终能否让人过得体面、有尊严,才是评判它的真正标准。
不妨放下那些简单的标签与成见,重新审视曾被历史短暂走过、却还未来得及被真正理解的道路。真正值得留意的,从来不是表面的模式与口号,而是它们背后那种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定义,对公平、稳定、尊严的再追问。
或许,真正的改变,不是等谁来“掌舵”,而是人民终于学会了自己掌握方向。
来源:小小的治愈
本文初摘录于:2025-08-20,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5-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