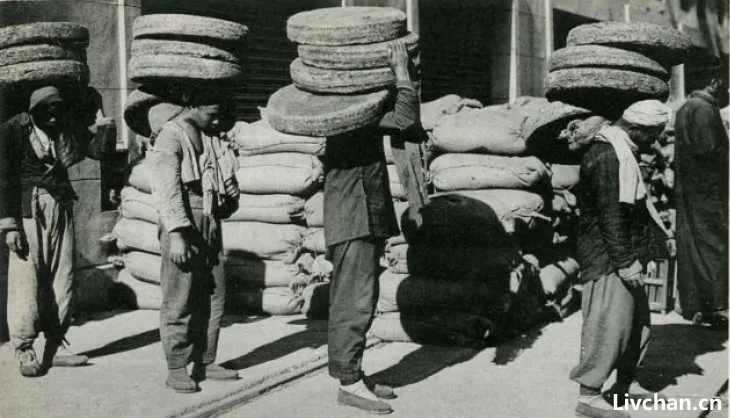资本早已给劳动者设好了陷阱:从一份假用工合同看工伤维权的荆棘之路
繁体资本早已给劳动者设好了陷阱:从一份假用工合同看工伤维权的荆棘之路
事件背景:2025年的5月的某天,宋某在石家庄太行南大街与南三环交口的西南角某工地干钢筋工,他昨天还在另一个工地给同一个劳务公司干活,当天上午被带班的叫到该工地,他在货车上卸钢筋的时候,不小心掉落,下面正好有一个梁底(注:突出地面的一种结构),把他的胸椎,腰椎当场摔成椎体骨折。(注:事后经石家庄某省级三甲医院检查结果。)
当他忍着剧痛向单位索要赔偿时,得到的却是一份从未签字的"用工合同"——这份事后补办的文书,像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突然罩住了他所有的求助路径。

这不是个案,而是无数工伤劳动者维权路上的缩影:资本早已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操作,为劳动者设下了层层陷阱,而劳动法规的阳光,往往需要穿透太厚的阴霾才能照进现实。
一、陷阱的起点:从"用工关系"到"假合同"的身份迷局
资本给劳动者设下的第一个陷阱,是模糊劳动关系的法律定性。
在当下的用工市场中,"用工合同"与"劳动合同"的一词之差,成了很多企业规避责任的利器。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核心凭证,意味着用人单位需承担缴纳社保、支付经济补偿、落实工伤待遇等法定义务;而一些企业刻意使用"用工合同",试图将关系定性为"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以此逃脱劳动法的约束。
更恶劣的是如劳动者遭遇的"假合同"——既未让劳动者签字,又在事故发生后补签伪造,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旦发生工伤,便拿出这份"证据"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让劳动者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
这种操作本质上是对法律的技术性规避:他们深知,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前提,而证明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往往压在弱势的劳动者身上。
二、陷阱的深化:工伤维权中的证据枷锁与程序壁垒
当劳动者突破身份迷局,试图通过工伤认定维权时,资本设下的第二重陷阱便浮出水面——证据链的刻意断裂与程序的人为复杂化。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需以劳动关系存在为前提,而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本应由用人单位举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但现实中,企业往往通过不签合同、不发工资条、不缴社保、甚至让劳动者用他人身份打卡等方式,销毁一切能证明劳动关系的痕迹。劳动者不得不四处搜集工资转账记录(往往是私人账户而非对公账户)、工牌(无单位公章)、同事证言(同事因怕被辞退不敢作证)等"碎片化证据",每一份证据的获取都如同在荆棘中前行。
即便劳动关系得以确认,工伤认定环节仍有陷阱。一些企业会拖延提交工伤认定材料,甚至伪造考勤记录证明劳动者"非工作时间受伤";当劳动者自行申请认定时,又会以"未收到通知"为由提起行政复议,将程序无限拉长。有数据显示,我国工伤维权案件的平均耗时超过11个月,远超普通劳动争议案件,很多劳动者在漫长的程序中耗尽积蓄与精力,最终不得不接受远低于法定标准的赔偿。

三、陷阱的根源:资本逐利与监管缝隙的共谋
这些环环相扣的陷阱,本质上是资本逐利本性与劳动保护监管缝隙共同作用的产物。对于企业而言,不签劳动合同可节省社保成本,不认定工伤可规避巨额赔偿,而违法成本却极低——根据《劳动合同法》,不签合同的惩罚仅是支付双倍工资,且有时效限制;伪造合同的法律责任更难追究,劳动者往往因缺乏鉴定费用而无法证实合同虚假。
与此同时,基层劳动监察力量的不足,也让资本有机可乘。一些地方劳动监察大队面临人员少、任务重的困境,对企业的日常监管难以覆盖;劳动仲裁虽为维权途径,但受制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劳动者在证据博弈中天然处于劣势。这种监管与救济的滞后,使得资本敢于铤而走险,将法律漏洞转化为对劳动者的系统性压迫。

四、陷阱的延伸:工资拆分里的逃税与证据湮灭双杀
用人单位在工资发放上的操作,更暴露了资本规避责任的深层算计——将实际超过5000元的工资拆分为两人头发放,使每人金额均低于个税起征点,表面看是"帮劳动者省税",实则是一场兼顾逃税与湮灭劳动关系证据的双重操作。
这种拆分的核心动机有二:一是逃避社保缴纳义务。
社保缴费基数以工资总额为基准,拆分后申报的"单人工资"远低于实际收入,用人单位可按低基数缴纳社保,甚至只给拆分后的"其中一人"参保,另一人则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一旦发生工伤,未参保的"虚拟人头"自然无法通过社保报销,而参保人的缴费基数与实际工资脱节,也会导致工伤待遇(如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补助金等)按低标准计算,劳动者即便维权,也只能拿到远低于法定标准的赔偿。
二是规避个税与制造证据混乱。
通过拆分工资,用人单位既少缴了企业应承担的个税代扣义务,又在形式上让劳动者"免缴"个税,以此麻痹对方配合。但更隐蔽的危害在于,这种操作会彻底摧毁工资凭证的真实性——工资单上的姓名、金额与实际劳动者完全脱节,银行流水中的付款方可能是私人账户,甚至与拆分后的"另一人头"毫无关联。当劳动者需要证明劳动关系或主张实际工资时,这份假工资单会成为最棘手的障碍:仲裁委或法院难以将拆分后的金额合并认定为实际工资,甚至可能因"工资发放对象与劳动者不符"而质疑劳动关系的真实性。
更荒诞的是,这种操作会让劳动者陷入"自己否定自己收入"的悖论:若主张实际工资为拆分后的总额,需证明两人头的工资均归自己所有,这往往需要提供额外证据(如与拆分对象的约定、实际收款记录),而这些证据的获取同样受制于用人单位的配合;若默认工资单上的金额,则意味着接受低标准的工伤赔偿,甚至可能因"工资过低"被质疑与工作强度不符,间接削弱劳动关系的可信度。
从法律层面看,这种拆分行为已涉嫌违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规定,伪造、变造账簿或记账凭证属于偷税,一旦查实需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并面临罚款;而《社会保险法》也要求用人单位如实申报工资总额,瞒报、漏报将被责令补缴并加收滞纳金。但现实中,劳动者往往因担心失去工作而被迫接受这种操作,直到发生工伤才发现,这份"避税工资"早已为维权埋下致命陷阱——连证明自己实际收入的凭证,都成了用人单位精心伪造的"证据"。

这种工资拆分的把戏,本质上是资本利用信息差与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将劳动关系从"书面契约"进一步降维为"地下交易"。当工资单、银行流水这些本该最直接的劳动关系证据都被人为篡改,劳动者在维权时就如同站在一片被刻意搅浑的水域中,连证明"自己挣了多少钱"都需要一场艰难的战斗。
五、刺破陷阱的微光:劳动者的武器与制度的完善
面对资本设下的陷阱,劳动者并非毫无还手之力。那些工资转账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装工牌、甚至就医时用人单位垫付费用的凭证,都是刺破"假合同"的利器;同事的匿名证言、车间的监控录像(若能设法获取),都能成为证明劳动关系的关键。而《工伤保险条例》中"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的条款,更是劳动者可利用的法律盾牌。
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完善刻不容缓。一方面,需加大对伪造劳动合同、故意销毁劳动关系证据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另一方面,应简化工伤维权程序,建立"劳动关系推定"机制——对于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基本特征的案件,可先推定劳动关系存在,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反驳责任。唯有如此,才能让资本不敢轻易设下陷阱,让工伤劳动者的维权之路不再布满荆棘。
从一份假用工合同到工伤维权的重重阻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力量失衡的缩影。当法律的阳光真正穿透每一个陷阱的角落,劳动者的尊严与权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这或许是无数工伤维权者用血泪换来的启示,也是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方向。
来源:海阔天空
本文初摘录于:2025-08-19,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