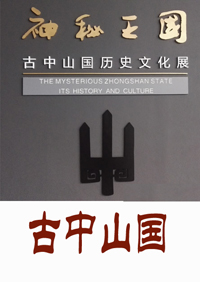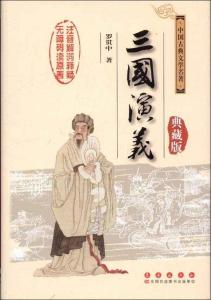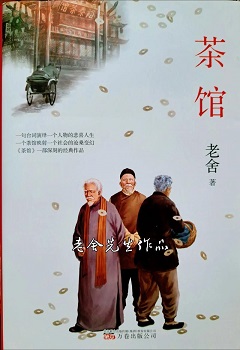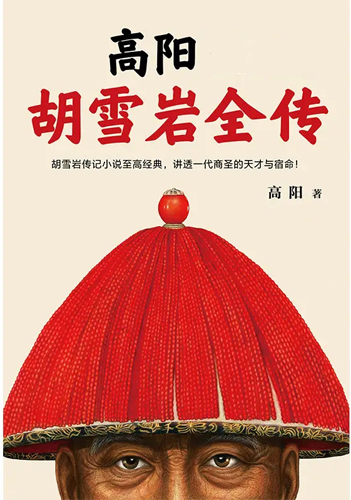6月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他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此后,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6月9日,贺龙因病逝世。他在去世前对夫人薛明说:
“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关于贺龙之死,一位署名为“靳卫”的中央警卫师权威知情人在《贺龙逝世前一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贺龙元帅》一文所描写的贺龙在“文革”中受非人折磨的情节是假的,是编出来的。其描写和“文革”结束后所拍的电影《元帅之死》类似。当时我们警卫师2团2营组织看电影《元帅之死》,下边一片嘘声,说这影片不是瞎编吗?全体官兵非常生气。看待“文革”应该实事求是,不能瞎说。
贺龙“文革”中休息不再工作后,也就是“靠边站”后,他的警卫工作是由我营4连一个班担负的。一个小院住贺龙和警卫班,并没有他的夫人薛明,怎么会迫害他夫妻二人呢?夫人隔一段来看一下,开始来的勤些,后来来的少些。毛主席和周总理很关心贺龙,要求照顾好,每天按时向团师卫戍区汇报。连队派一名炊事班副班长专职为贺龙一个人做饭。这个副班长炊事技术很好,连首长专挑的。专职为贺龙采购食品。贺龙的伙食费开始每月约80元,连队干部战士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费是13.2元,3年后才涨到13.32元,后又涨到13.35元,10年后涨到13.45元,算是涨到顶了。这个标准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好几年。每个月长0.1元时,连队还专门召开了全连大会,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说贺龙当时每月的伙食标准相当于6个战士的总和,生活很好,每顿至少二菜一汤或四菜一汤,一荤一素或两荤两素。每顿饭做好,警卫连换班到连队吃饭,副班长只做不吃,只尝咸甜酸辣味道。
过了一段时间,贺龙嫌面食多,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是南方人,爱吃大米,伙食调剂一下。毛主席收到贺龙信后,专门批示给中央有关部门:“贺龙过去有功,要照顾安排好贺龙的生活,每月按200元生活费标准”。这个批示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对所有老干部都要照顾好生活。
毛主席批示后,贺龙的生活更好了。连队专门研究制定了贺龙每周食谱,基本上一周不重样,顿顿都是四菜一汤。有时吃不完,副班长想吃又怕违犯纪律,就用小桶提着当泔水喂猪了。哪里有贺龙临死说“想吃猪耳朵”这回事?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猪肝猪蹄子,哪一样都不少。副班长经常征求贺龙的意见,他说想吃啥就弄啥。一个月200元,他一个人相当16个战士的伙食费。当时猪肉每一斤0.5元,贺龙的伙食好到天顶上去了,酒是好酒,成瓶子放着,想喝就喝,现成的。茶叶是龙井茶,配了两个暖水瓶,喝不完晚上洗脚用了。有的文章和电影描写成贺龙渴得拿碗伸到墙外接房檐水喝,有病不能治,受百般折磨,这压根是胡说。定期为贺龙体检、洗澡、订报纸、听广播,每天给他打扫卫生。他每天室内室外、院内院外散步打拳锻炼身体、做深呼吸、吐故纳新。他需要看病时,来专车接送,警卫班专职保护,师部警卫参谋甚至有时警卫科长副科长专程护卫,看病是部队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住高干病房,特级医护。
要说贺龙元帅有委屈的地方,就是不管事了,心里闷,精神上有压仰,这也是“文革”时期部分老干部的共同感。但是老干部的工资是照发不误,每月几百元,应该说衣食无忧。现在说的“文革”时期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住牛棚”,实际是到“五七”干校种地,劳动缎炼,消除官僚主义,并不是真住在牛棚。住牛棚,是个形容词。当时邓小平到江西省劳动缎炼,住的“牛棚”是一个南昌市郊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两层将军楼。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用专机把邓小平夫妇送到住地,由当地炮兵团派出一个12人的警卫班,并由一位军官带队和1名战士值班,和邓小平同住在独楼独院的将军楼,专职为邓做保卫工作。邓到邻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锻炼,往返步行,工厂专门又成立了邓的党员保卫小组护卫。邓每月400多元工资照发,也可以喝到茅台酒。所以说,即使在“文革”时期,党和毛主席也是非常关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当然,极少数受到人身迫害也是事实,也是有的。刘少奇疏散到开封,因他长期患有肺炎,一个多月时间,毛主席、周总理4次派中央医疗专家小组到开封为刘少奇会珍治疗,最好的药都用了,但终因刘年老病重,医治无效病逝,并非人为迫害而死。
上述我说这些,都是有当时的值班记录的,都是有历史档案可查的。希望现代的文学作品尊重历史,胡编乱造经不起历史检验,是会让后人笑掉大牙的。
再说贺龙逝世之时,毛泽东还在武昌梅岭1号。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颂他“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对工作人员说: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九大”纪录片时,看到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很生气地站起身来退场,并且说:
“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
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文件中规定: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26日,毛泽东要离开武昌了,他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谈话说:
“下去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50%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毛泽东最后说:
“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忆说:“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曾思玉等人还曾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问他们去过三峡没有,大家都说没去过。毛泽东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
此外,毛泽东在武昌期间,还曾询问了焦枝铁路的建设情况以及江汉油田会战的情况,又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6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谈话,他说:
“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笔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
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
此前,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他把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后半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道:“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最后批示:“可发。”
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
“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7月间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跟着周恩来去外地见毛泽东。
此前,李德生担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之职,同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自7月起,他又接到新的通知,要他兼职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这一天,李德生是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免不了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泽东见他如此,便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桌子上的眼镜,戴了一下,亲切地问李德生戴不戴眼镜?又问他看什么书?还建议他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周恩来见李德生的情绪在毛泽东不经意的言谈中平复了许多,便向毛泽东汇报说:
“主席,李德生同志已经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小心地插话说:
“主席,我的职务太多了,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
7月8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
“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
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浙江的工业配置情况及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又谈到了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7月11日,陈毅等人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
早在4月底,毛泽东让陈毅到石家庄一家工厂去蹲点,交代他两项任务:一是到工厂总结经验,给“斗批改”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召集几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上述报告便是他和几位老帅讨论的结果。
7月22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6、7期合刊发表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及编者按。
《红旗》杂志编者按说:“这篇调查报告值得一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工人阶级,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精兵简政;对原有规章制度一分为二,保留合理的,改革不合理的,创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注意政策,步骤上积极而稳妥,这些经验可供参考。”
报告中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根本上。”
1969年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铁列克提伏击中国边防军1个排,中国38名巡逻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八一三”流血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嚣要“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打击。”
8月20日,勃烈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要他向尼克松或基辛格征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多勃雷宁当晚紧急约见了基辛格。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来到白宫,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尼克松说:
“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子上,说:
“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
“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这样做。”
尼克松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尼克松说: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尼克松等人得出结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什么花招。尼克松最后决定:
“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新闻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烈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基辛格则不无担心地说:
“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
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认真搞好斗、批、改。”
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胡志明病情加重,立即派出第2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早在1969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获悉胡志明患了重病,就派去了第一个专家医疗组。
8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中批评了“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说法。社论中还写道:
“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
8月26日,中国第3个专家医疗组赴越南。
8月27日,国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防空小组。
8月28日,毛泽东先后批准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
欲知毛泽东如何粉碎苏修叛徒集团突然袭击的阴谋,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贺龙之死,本章引用了署名为“靳卫”的中央警卫师权威知情人士撰写的《贺龙逝世前一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一文,加以佐证。文章中说:《贺龙元帅》的作者所描写的贺龙在“文革”中受非人折磨的情节是假的,是编出来的;其描写和“文革”结束后所拍的电影《元帅之死》类似。当时我们警卫师2团2营组织看电影《元帅之死》,下边一片嘘声,说这影片不是瞎编吗?全体官兵非常生气。看待“文革”应该实事求是,不能瞎说。这篇文章通篇都很好,值得那些受骗的读者和观众好好地读一读。将历史事实公布于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做人的底线。可那些谎言家宁肯步德国法西斯头目戈培尔的后尘,相信“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一个接一个地以谎言治史,也不怕遗臭万年,岂不是蠢而又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