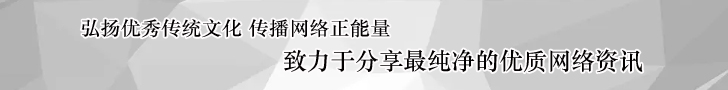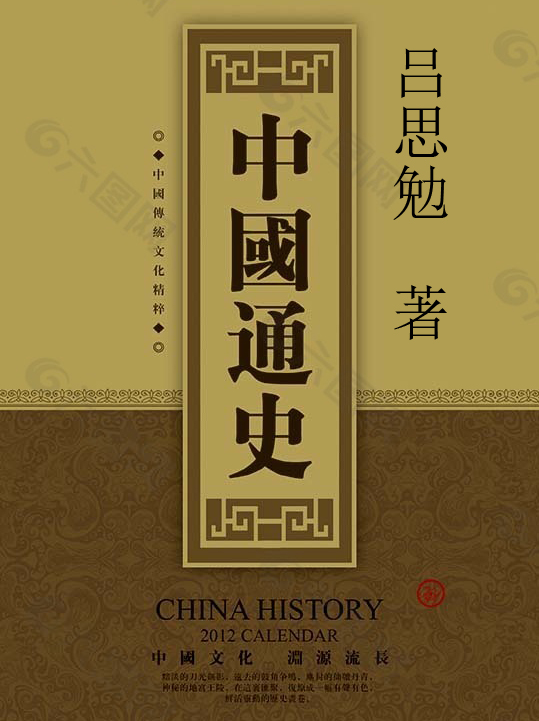第七章 赴开封抢堵黄河 节开支杀鸡骇猴
林则徐是在英军再陷定海的时候到达黄河决口工地的。他在扬州府所属的仪征县接到署理江苏巡抚程矞采转来的上谕,“着免其遣戍,即发往河东效力赎罪”。
得到消息,一家人都很高兴,仪征知县也来贺喜:“林公,治河有功,论功行赏,不难官复原职,至少遣戍新疆可免。”
“借邑尊吉言,但愿能够治河有功,救民于溺饥。我明天就起程北上,今夜起草谢恩呈,请南河总督代奏谢恩。还请邑尊行个方便。”林则徐已是戴罪之身,没有上折的资格,但皇恩还是要谢的,只能由地方大员代奏。南河总督全称是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管辖江苏、安徽等地黄河、淮河、运河防治工作,驻节清江浦,林则徐的谢恩呈便就近由仪征县的驿差顺便带往清江浦。
封堵决口非一日之功,三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有可能,林则徐前往肯定要昼夜靠在河工上,家眷跟着徒增困扰。他让郑夫人及儿子、儿媳等家眷返回南京寓居,他只带一名仆人北上。郑夫人放心不下他的身体,但他主意已定,她只好率儿子儿媳折回南京。
由于黄河洪水漫流,皖北豫南几成泽国,许多地方道路不通,林则徐和仆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祥符。中原沃野,已成汪洋,路上全是灾民,水中则浮尸如麻,情形极为凄惨。
黄河大堤为了便于修治,分段设堡,数十堡设一汛,数汛设一厅。开封段南岸堤工由下南厅统辖,分为东西二汛。西汛自西而东,设三十三堡,第三十一堡在开封西北十五六里,地近张家湾。此次黄河决口就在张家湾附近。
负责督办河工的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驻在张家湾东的陶家庄关帝庙。庙建在一处高地上,无淹没之虞。
林则徐由祥符县的差役头前带路,来到关帝庙。刑部郎中蒋方正、内阁中书张亮基在庙门口迎接,两人都是随王鼎前来办差。庙为三进,王鼎就住在第二进院内。他和通政使慧成还有河南巡抚牛鉴在院内迎接。王鼎已经七十五岁,二十多天前到了祥符,备受煎熬。林则徐鼻子一酸,眼眶发热:“老相国,前年一别,你苍老多了!”
王鼎说:“黄水滔滔,百姓为鱼鳖,我却束手无策,岂能不老?你来了就好了。”
牛鉴与林则徐同庚,时年五十七岁,不过看上去倒好像六十有余。黄河决口,他这地方大吏自然首当其冲。开封被洪水围困两月,他有一个多月驻在城墙上,指挥堵御决口,疏导水势,又要救助灾民,缉捕盗匪,真正是焦头烂额。八月十五后黄河水势稍落,开封城三个城门才不再进水,危情缓解,他今天专程到钦差行辕,是商议着手抢堵大堤决口。牛鉴做了多年的京官,林则徐在京时与他多有交往,两人都属清廉耿直的官员,物以类聚,关系不错。牛鉴说:“少穆,你是治水的行家,你来就好了,帮王相国出出主意。这次大堤决口太大,大家都束手无策。”
林则徐说:“我奉旨到河工上听候相国和抚台的调遣,自然敬听号令。”
王鼎说:“少穆,你也不必推辞,都知道你是治河的好手。如今黄河大堤决口有数百丈,到底该怎么抢堵,包括文河台,我看也是不甚了了,何况他又被革职,你要多多偏劳。”
文河台就是东河总督文冲。东河总督的全称是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黄河决口,文冲难辞其咎,先是交部严议,后来是革职留任,前天刚接到上谕,革职并在河工上枷号示众。此时他正在大堤上示众呢。朝廷新任命的东河总督是江苏淮扬道朱襄,他此时正在路上,东河总督暂由王鼎兼领。王鼎对治河毫无经验,文冲手下的人都在观望,整个河工几乎是群龙无首。
林则徐问:“现在河上正在忙什么?相国和抚台是什么打算?”
牛鉴说:“现在正盘算收购埽料。”
所谓埽料,就是护堤堵口的材料,用秫秸或者柳枝裹入石块、砖头捆扎而成,到时候沉到水里,用以护堤、堵口,其中用得最多的是高粱秸。因为堵口所需埽料量非常大,总是先大批收购,堆在河堤上下,称为埽垛。一垛一般长六丈,宽至一丈五六,每垛大约五万斤左右。埽料用量极大,动辄数千垛,收埽也就成了争相伸手的肥差,贪官污吏们往往上下齐手,大做手脚。
林则徐问:“现在不知收了多少?”
牛鉴说:“没有多少。豫南一带高粱秸尚未长成,就全被水淹;豫北没有被水,却遭到旱灾,秸料减产。”
林则徐又问:“河上所备埽料有多少?”
每年汛期前,黄河下游沿堤都会备下埽垛,以备抢险。祥符决口,上下游所备的埽料尽快运来,是最便捷的办法。
牛鉴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千把垛总该有的。开封被水围困两月,东北隅城墙坍塌数十丈,北、东、西三门都屡出险情,急需埽料,数次与文河台商调,到目前只调到三十余垛。”
原因嘛,巡抚守土有责,要抢护省城,但河道上的人职责是守黄河,汛期未结束,随时有决口的风险,当然不会雪中送炭,把埽料送到开封来。如今决口处下游的黄河已经断流,水路不通,陆路又被水淹,运输不易。还有一条,埽垛从甲地运到乙地,只有点运输费,不如新购花头多,自然也不积极。
林则徐问:“现在河上,引河挖了多少?”
河堤决口,水流冲口而出,原河道断流,这时必须把原河道深挖,称为引河,以便引导河水归复旧道,减少决口处的径流,这是堵口成功的关键措施。
王鼎说:“尚未开挖,这两个月全副精神都在解救开封。”
决口已逾两月,竟然还没有开挖引河,显然另有原因。
王鼎说:“主要是对治河的办法大家各有看法,未能定议。”
黄河决口后,开封城冲毁严重,河督文冲束手无策,建议放弃开封,把省城迁到洛阳,待黄河横流减势后再求补救。牛鉴开始也赞同这一主张,但后来征询百姓意见,虽然十之六七人家都遭了水灾,但故土难离,真正愿意迁走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他顺从开封士绅所请,上奏反对弃城。王鼎到开封后,登上城墙,但见城内城外黄水浩荡,也有放弃省城的打算。但开封士绅多次跑到钦差行辕来痛哭流涕,恳请不要弃城,而文冲及河工上的人都认为要抢堵决口实无把握。王鼎两头为难,弃城不忍,抢堵无术,至今尚在游移。
林则徐说:“相国,绝对不能放任自流,我从南边过来,一路上惨不忍睹,必须设法抢堵,束河复归旧道。”
黄河因为挟带泥沙量大,善淤善决,有时北流入渤海,有时南流入黄海。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在阳武决口,夺泗水,入淮河,在云梯关入黄海,到道光二十一年,已经夺淮入海六百六十一年,其河道基本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也就是从开封斜向东南入海。这次在开封决口后,在河道以南泛滥,最后流入洪泽湖。林则徐认为,如果任由黄河水泛滥,长期注入洪泽湖,那么洪泽湖被泥沙淤积,决口而出,河之南、江之北全成泽国,千百万生灵深受其害。
王鼎点头说:“啊,洪泽湖会因此成害,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
牛鉴说:“相国,省城有三不可迁。一则百姓安土重迁,被灾以来,迁出者多系商贾客民,或者城外有亲族可投者,近日水落,回城者络绎不绝,真正愿迁者十不及一。二则百姓在水灾来时,捐钱捐物,全力抢堵,四城士绅更是自发抢堵城门,登城巡查。此时水已降落,再议迁省,岂不令汴梁百姓心寒?三则一旦议迁,轻举妄动,百姓至愚,以为城不可保,官已驰防,产业不可保,生计无可谋,四出窜逃,仓皇靡止。无赖棍徒乘机抢夺,赤手游民随时附和,恐怕从前急公效力之义民,将变为劫掠作乱之奸民。祸生不测,只在须臾。”
林则徐说:“还不仅如此。如今英夷侵扰沿海,本已民心浮动,如果任由黄河泛滥,受灾百姓乘机啸聚,那就是泼天大祸。相国,这可是危及社稷的天大隐患!”
“是是是,城不可迁,河不可漫,我主意已定。”王鼎说,“只是文河帅上奏议迁,皇上也有此意。”
朝廷拨下一百七十万救急工银后,道光帝受文冲影响,随后下谕说,“百姓困苦情形已堪悯恻,设使水势日长,急切不可能消退,而城垣断不能久泡无妨,百万生灵俱归沉没,朕心实有不忍。与其拆移砖石,剜肉补疮,徒事祖苴,终难保护,莫若取所拨库银以为迁徙赈济之需。”
王鼎对牛鉴说:“镜堂,建议迁省,是你和文河帅联衔出奏,为什么改了主意,理由必须说充分,不然皇上那里要碰个大钉子。”
牛鉴说:“相国,我从来没有迁省之意!六月十六日我听说张湾水涨,就赶到堤上,十九日听说水已进城,我连夜赶回,紧急派人送信给河帅,说明省城危机情况,让他赶紧调拨埽料,派河营前来护城。谁料他把我的意思当成他迁省的佐证,所谓联衔出奏,我根本连折稿也没见到。省城受灾两月,河帅竟然未进省城一步,并未亲见水势消长,他的折子,不过是悬揣臆度。哪里像相国,到汴不过半月有余,已三进省城,省城情形,相国无不清楚。”
于是又详细分析省城不可迁的原因。
王鼎被说服了,点头说:“好,我下午就让人起草奏稿,定议省城可守而不可迁,决口可堵而不可漫。”又转头对林则徐说,“少穆,文河帅一直坚持说决口太大抢堵万难,上宪如此,手下的人可想而知。决口到底能不能堵得上,怎么抢堵,我可是门外汉,你可要偏劳了。我知道你舟车劳顿,按理说应该让你休息几天,可水患无情,你明天就到堤上去,勘察形势,出出主意。”
林则徐说:“好说,我来就是为相国效力的。只是,需要有一个了解当地情形,又懂治水的陪同才好。”
王鼎说:“河道上的人,本不乏明白人,可是他们心里的小九九太多,言不由衷,十分可恶。”
牛鉴说:“我推荐个人,那就让开封府邹钟泉太守陪你好了,他在河工上干过,很有一套。这次抢护省城,他功不可没。”
邹钟泉就是开封知府邹鸣鹤。他是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进士,当年即用知县,分发河南,已经在河南任职十九年。他任兰仪厅河工同知五年,治河有功,擢知府,历任卫辉、陈州知府,前年调任河南首府开封。黄河决口后他不同意放弃开封,天天露宿开封城墙上,率百姓全力防堵,总算保住了开封没被全淹。林则徐决定第二天就去开封见邹鸣鹤。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林则徐在巡抚衙门巡捕和河道下南厅一位叫高步云的文案陪同下,先到大堤上看看情况。林则徐任过河南布政使、东河总督,对黄河大堤的情况并不陌生。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裹挟了大量泥沙,有一石水六斗泥的说法。黄水滚滚东来,一出了洛阳,便是落差极小的平坦平原,泥沙逐渐沉积,淤高河床,开始出现河面高于地面的情况,就是俗称的“悬河”。祥符这一带的悬河最险,河身比堤外平地高数丈,比开封城更是高出四五丈,一旦决堤,其害极大。
下游的黄河大都有两道堤,一道是大堤,大堤之内是大片肥沃的滩地,往往宽数里,最宽的达到二十几里。黄河平时流量很小,到了汛期才迅速增大,大堤内的大片肥沃滩地,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水的。农民就在这些滩地里种上庄稼,为了防备庄稼被淹,就沿河槽在滩地再建一道堤,称子堤。这次黄河决口,先是冲决子堤,然后大水漫滩,在张家湾附近漫过大堤,开始外流,进而冲刷决堤。
林则徐登上大堤,内外形势一目了然。黄河河槽已经断流,河水从数百丈宽的决口处灌向东南。他指指河槽问高步云:“黄河河槽离大堤有七八里路远,就是冲毁子堤,要漫过大堤,进而冲决大堤,总要好几天的时间,竟然一点防备也没有?”
高步云说:“张家湾这段大堤,属无工之地,全靠沙土夯筑,汛期到来,厅里曾经请求河帅划拨护堤经费加固堤防。河帅不以为然,认为厅里是胡出主意,希图贪墨。他终日与心腹属下饮酒作乐,别人根本说不上话。”
巡抚衙门的巡捕向林则徐介绍,高步云的哥哥就是南下厅同知高步月,就是他提出建议而遭否决。
高步云说:“这次大灾,是天灾,更是人祸。”
据高步云说,子堤决口后,高步月目睹水势浩大,怕冲开大堤,省城受害,出三百贯钱付给河营防守河堤,河营守备则“尽肥己囊,归家聚赌”。开封城外还有一道护城堤,本来也归河营防守,大堤决口后,布政司张祥河与知府邹鸣鹤赶赴城西北护城堤,发现河兵无一人值守。
林则徐感慨说:“河道上懈怠如此,怎能不出事!”
他们离决口还有一两里地,远远看到大堤上人头攒动。高步云说,河工上正在决口处修“裹头”——就是在决口的堤头通过抛掷石块、固定埽料等办法加固堤头,以免决口扩大。林则徐决定到决口处看看,走了一多半,看到堤上有人戴着枷,站在那里指挥,高步云说:“那就是文河帅。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被革了职,这才来修裹头。”
林则徐怕见了文冲尴尬,不再往前走。但已经来不及了,文冲打发人跑过来问高步云:“河帅问你,陪同的是什么人?”
高步云说:“是林大人。”
来人说:“河帅估计得不错,河帅请林公过去说话。”
文冲是满人,当过永定河道,在治河上并非门外汉。林则徐想见见也好,听听他的意见。他们几个人往前走,文冲则迎过来。等走近了,文冲因戴着枷,无法拱手见礼,点点头说:“林公,你何时到的?”
林则徐说:“昨天到的,没来得及看河帅。”
文冲哈哈一笑说:“我和你一样,已经是戴罪之人,当不起一声河帅了。林公,你在虎门一把火烧掉英夷两万余箱鸦片,真正是大快人心。”
虎门销烟,其实并未用火,但世人大都以为是放了一把火。林则徐微微一笑说:“不知情的人以为是我惹来海衅。”
文冲说:“鸦片害国误民,当烧!何错之有?就像我建议放弃省城,也是为国利民,只是不能为人理解。不过,公道自在人心。林公,你是治水的前辈,王相国又特别赏识,你在王相国那里,可要多多进言。”
林则徐说:“河帅,我也是戴罪之身,到河工上来效力,唯有听命而已。河帅主张迁省、暂不堵口,我很愿听听河帅的高见。”
文冲说:“水往低处流,是水的天性。开封城地滨大河,低于大坝数丈,岸崩具建瓴之势,城卑有游釜之忧,自古以来,为害最烈。其地本不宜作省城;至于暂不堵口,是顺势而为,而非不为。黄河已经奔向东南,自然会寻到入海口,以历史的经验,河水自涮河道,畅通无阻,可有数十年安澜,暂缓挽堵,不单可省下游三省十余厅修守钱粮,借此淘刷尾闾,亦可渐斯通畅。如果非要堵口,必然要在决堤处修堤坝,而且决口处至河槽俱系深塘,在此段复堤,土工量何其大也。我咨询过熟谙修防官弁,都说黄河盛涨漫滩时,河身最窄处亦须三千余丈方可容纳河流。此段黄河河身宽不过三千丈,如果再建堤坝,势必束窄河身,与水争地,阻滞河流,非长久之计;如果仓促抢堵,急于挽河水归故道,就像倒涌河流使之就上,需费何其大也,且头悬利剑,将来防守断无良方,漫溢之灾更烈。不如暂缓堵筑,待河水行走一两年后,再行查看办法。夹水堤防,本属违水性之下策;顺流疏导,乃大禹之良谟。这在我朝也有先例,如嘉庆十八年睢工漫口,至二十年始行堵合。”
林则徐点头表示受教了。文冲陪他到决口处察看,整个决口长有二三百丈,河水分三股从决口处冲向堤外,向东南流去,在平原上形成宽达十余里的水面。文冲说:“林公,这是水小了些,水涨最大时,水声轰鸣,犹如天崩地裂。你看河身比堤外高达数丈,让此滚滚洪流再归旧道,何其艰难?这一片土性疏松,方圆四五里,都是如此,就是勉强恢复大堤,将来还是险工险段。”他向东指指说,“由此往东,全是悬河,就是勉强再归旧道,处处防守,年年备险,这总不是办法。”
林则徐从大堤上下来,高步云说,由此去开封,有十五六里,到前面一个小高地,有一个临时码头,可以雇到船。
船小流急,三个人都有些提心吊胆。后来,看到前面有断断续续的堤岸。林则徐问高步云:“那应该是护城堤吧?”
高步云说:“是呢。这护城堤,这次可把开封城害苦了。”
这话是怎么说的?
因为开封北面就是悬河,元代开始,在城外就曾经修过护城堤,但后被水冲圮。明朝名臣于谦巡抚河南的时候,就在城西、北、东三面修了护城堤,离城都在五六里地左右。后来巡抚河南的都御史王暹又补筑南堤,这样开封四面都建起了护城堤。经过后人多次加修,护城堤达到高两丈五六,顶宽三丈,底宽十余丈的规模,后来黄河几次溢水或决口,护城堤都把河水挡在堤外,开封免于水灾。可是这次水太大,在护城堤西北部冲开一个决口,大水直奔开封城,顺着西城根灌注东南。开封城的地势总体上北高南低,中间高四周低。南面城墙上留有水门,结果河水从水门倒灌入城,分东西两路淹到城北。后来趁水势稍缓时把水门堆塞了,城外的水总算不能进城。可是,后来随着河水不断涌进护城堤内,水越积越深,开封四面被水围困,城墙东北隅坍塌,险象环生。巡抚牛鉴曾经派抚标中军率人去掘开南护城堤泄洪,可是堤外百姓坚决不许掘堤,结果开封城在水中泡了一个多月,直到河水在护城堤东南苏村、红沙湾两处破堤而出,水面下降,开封城才总算转危为安。
小船从护城堤西北角顺流往东,开封城遥遥在望。眼前全是泥滩,不时看到露在外面的屋脊、树梢,偶尔也有斜插入泥的船尾或桅杆。高步云告诉林则徐,开封城外淤泥有的深达数丈,浅处也有三四尺。城外村庄无一幸免,居民被淹毙者十之四五,在护城堤附近居住者比较幸运,都跑到堤上去躲过一劫,但多半来不及携带衣粮;其他村落就更惨了,或者爬上屋顶,或者攀到树上哭救哀号,无奈无人可应。往往数日吃不上一口饭,喝不上一口水,或者饿死屋顶,或者饿极了投水自尽,真是惨不忍睹。有人乘船想逃走,但水势太猛,不少船被打翻。
船到了开封城的西北角,这里顺着西城墙建了三道挑水坝,导引河水东流。城外淤泥离城墙顶只有三四尺,城北门附近,已经用土石垫起了一个坡道,人、车可直登城墙。城墙上的雉堞在大水漫城时全都拆光用于抢堵,成了光秃秃的平顶;所有城门楼也都拆光,只余木架,上覆席片做官棚。
高步云说:“水冲决护城堤后,六月十六日晚到达开封城下,登城一望,月光照耀,势如滚雪,一喷数丈。四面只听得如雷如钟,轰轰作响。当时牛抚台不在城中,张藩台、况臬台、邹太守等官宪纷纷登城,分工抢堵城门。无奈埽料奇缺,就把城堞、望楼全拆了,后来几次水涨遇险,又拆贡院,先是围墙,后是经房、主考房、内外监试、提调及各所房屋,十天前,河水再次猛涨,又把一万余间号舍全数拆除,如今只存大门和明远楼了。”
河南贡院林则徐再熟悉不过,雍正年间扩建,号舍一万一千八百余间,明远楼高四丈有余,当时号称高广甲天下。科甲出身的人无不对贡院情有独钟,林则徐连连叹息说:“可惜了,可惜了。”
高步云说:“也是没办法的事。城墙一再遇险,西城外又要修挑水坝,埽料奇缺,一块砖卖到十二三文。”
小船在挑水坝边停下,这里有临时搭建的码头。他们跳上码头,踩着绵软的新垫小道到了北门附近。开封府的差役在此等候,说:“邹太守到东城安排清赈,派小的在此恭候林公。”
林则徐顺着土坡登上城墙,只见四面城墙都是人满为患,尤其是东城墙宋门、曹门附近,更是熙熙攘攘,犹如集市;往城内看看,只有东北隅和城中间有部分房屋没有被水,十不及二三,其他皆在水中,有的只余屋脊。
开封府的差役告诉林则徐,这次河水进城,灾情极重,除布政司署、粮道署、开归道署、开封府署和数条街道无水外,余皆深八九尺、四五尺,浅处也有二三尺。民房倒塌无数,百姓只能到城墙上躲避。有些商铺只好到城墙上买卖,曹门、宋门一带几成集市。
差役头前带路,在曹门城上见到了开封知府邹鸣鹤。他脸色黝黑,眼窝深陷,显然是操劳过度。但精神头还好,他说:“最近有人上书抚台,说放赈中弊端百出,地保借机渔利,开写虚名,随意冒领;衙役串通地保,冒领侵吞。近两个月,全城都忙着堵水护城,事出仓促,户口不清,里面肯定弊端百出。现在水势减落,可以稍稍喘口气了,腾出手来,安排人清查户口,一一核对。”
林则徐说:“邹太守两月以来衣不解带,夜宿城头,牛抚台和王相国都是交口称赞。邹太守一心为民,真是令人钦佩。”
邹鸣鹤说:“林公,过奖了,职责所在,应当如此。百姓称我们一声父母官,关键时候,怎么能弃民于不顾!”
林则徐说:“相国和牛抚台,都让我来向你请教治河的方法。”
邹鸣鹤连忙摇手说:“林公,你是治水大家,我何敢班门弄斧。实话说吧,牛抚台特意让你我见面,意不在此。他知道王相国对您极为信赖,是想通过您影响王相国,尽快拿定主意,不要再有迁省之议。”
林则徐说:“王相国昨天已经明确表示,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应堵不可漫,牛抚台当时在场啊。”
邹鸣鹤说:“相国来此半月有余,三次进城,迁省之议多次反复,牛抚台实在放心不下。我有开封六不可迁之议,抚台是想让你我见一面,以坚林公之志。其实,牛抚台是多虑了,以林公之智,迁省城、任泛滥,这样荒谬的事情怎么会看不透,何须我饶舌。林公,理由我不必说,你只听一听开封父老的声音,就知道城能不能迁,河该不该堵。”
邹鸣鹤站到一堆砖头上,大声说:“父老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喜讯,曾经任过咱河南布政使的林公,大家翘首以盼的林公来到开封了。”
他把林则徐拉到砖堆上,城墙上立即人声鼎沸,有的高喊林大人,有的说林大人来了就好了。邹鸣鹤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说:“父老乡亲们,林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开封城能不能弃?”
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不能!”
邹鸣鹤又问:“你们告诉林公,决口该不该堵?”
众人高喊:“堵,堵!怎么能不堵呢!”
有一个老者拉住林则徐的手说:“林大人,你当了几个月的河南布政使,河道总督也只当了三个月,可是俺们河南人都服你,你是个能人,你能把河道上的人治住。一个月前听说朝廷派你来开封,俺们都说,林大人来了就好了,都盼着你来呢。”
林则徐说:“老人家,我如今是罪臣,是被朝廷派到河上来效力的。”
老人说:“咱不懂朝廷的事,只知道林大人是好官,只盼着你赶紧帮着堵住大河。”
林则徐点头说:“老人家放心,我会尽力的。”
邹鸣鹤陪林则徐下了城,到开封府去小坐。他说:“林公,开封府出了个包龙图,谁坐这个位子,都不敢愧对良心。”
说起治河的事,邹鸣鹤说:“河上的人真是靠不住,全都钻到钱眼里。大水围城,开封五门全靠士绅主持填堵守护。后来牛抚台曾经把河营的几百人派到曹门去,让他们与士绅一起负责东城一带的救护,结果第二天士绅就向抚台请辞。原来河营的人嫌士绅办事认真,他们无可蒙混谋利,设法把士绅排挤出去。牛抚台心里明镜一样,坚决不答应。结果河营的人处处闹别扭。天下最烂的衙门就是河道上,最贪的官非河官莫属。”
林则徐最清楚不过,河道上的银子,每年都是数百万两,可是真正能用到河工上的,十不及二三,都被层层分肥,已经视为惯例。而且各级官员从河道上沾点光,也成了惯例。北上会试的举子,按惯例都可七攀八附,到河道衙门拜会,讨得一笔盘缠。“打秋风”一词据说就是从河道上起源的。
林则徐说:“咳,河道上腐败,尽人皆知,也不能全怪河上。黄河要抢堵决口,绕不过河道上,还必须用他们。”
邹鸣鹤说:“用,那是将来的事,再说,朱河帅还在路上,至于文河帅,恕我直言,此人自以为是,糊涂至极。我劝林公少与他和他的亲信属下接触,不然会受他谬论贻误。”
林则徐说:“王相国的意思,让我尽快调查一下河情水情,还说让我跟着你跑跑河上。”
邹鸣鹤说:“林公,你也看到了,我是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无法陪你。这样,我派两个人带一顶肩舆跟着你,你走累了就坐肩舆;再派一个略通文墨的帮你抄抄写写,然后再派两个人,负责带着绳尺,帮你测量。至于河道上的人,让高司马派个可靠的人陪着你好了。”
所谓高司马就是指高步云的哥哥下南厅知州高步月。他做了多年知州,对祥符段黄河十分熟悉,而且人品官声都不错。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但林则徐力辞了肩舆。他说:“邹太守,我是戴罪之人,坐着肩舆出现在河工上,那可真成了笑话。”
邹鸣鹤说:“林公,河工上苦,你是知道的,风里来雨里去,你已经五十有七,我担心你吃不消。”
林则徐说:“谢谢你的美意,我心领了。”
邹鸣鹤说:“林公,民间有句俗语,开封城,城摞城;地上城一座,地下城几层。魏国的大梁,唐代的汴州,宋朝的汴梁,金人的汴京,前朝的开封,一层一层,都在咱们脚下。黄河悬在头顶上,不是今天才有的局面;开封这个地方,屡毁屡建,却从没有放弃!绝不放弃,绝不向水灾低头,已经是开封人的脾性,也是开封人的傲气。不能从我们这里,变成了没有骨气的不肖之辈。”
林则徐感叹说:“邹太守还有这一层想法,实在难得。人最难得的是精气神,天塌地陷,只要精气神不倒,谁也难奈我何。你放心,我一定会极力向相国进言的。”
林则徐回到关帝庙,向王鼎报告了前往开封的情况。王鼎说:“我今天上午已经出奏,城可守不可弃,河可堵不可漫,这不必再议。现在关键是如何堵口。新任河帅还在路上,现任河帅已经革职,我这兼署河督,对治水是门外汉,所以少穆你得多用心,多偏劳。你不要觉得是戴罪之臣,不方便出头。没什么不方便的,你就是代表我在河工上办差,有什么建议你随时提出来,我去安排。这几天你就到河上多跑跑,如何堵口,拿出个方案来,我尽快奏报朝廷,尽快抢堵决口。”
王鼎如此重托,林则徐没有二话,带人在决口上下查访、测量,又向老河工、船工请教,前后用了五天,正式向王鼎报告了治河方案。张家湾附近土质疏松,且决口到子堤被河水淘出多处深塘,林则徐决定避开这里,从决口东西两侧斜向子堤方向筑新坝,即西坝斜往东北向子堤靠拢,东坝斜往西北向子堤靠拢,接近子堤后东西两坝合龙。同时,在河道下游开挖引河,以引导河水沿旧道东流;在合龙口上游修三道挑水坝,以减轻河水对新坝的冲刷。
林则徐画了草图,向王鼎介绍。王鼎说:“张家湾这一带土质疏松,历史上黄河有几次都是从这里决口。你这个方案,避开张家湾筑坝,很好,就是工程量要大不少。”
林则徐说:“是,我和下南厅的人粗略估算,西坝从马头起,东坝从小马圈起,两坝长约两千四百丈(一丈约3.3米);靠近子堤后是双坝,长三百丈;另外三个挑水坝共长一百六十余丈,初步估算埽料一项约需八千垛,工程量相当大。这还没算上山东、江苏两省开挖引河、抽沟的工程。”
黄河从开封到江苏入海,六百余里,要让决口的黄河顺利归复旧道,必须在决口下游深挖河道,便于洪水下泄,这称为引河;再往下,根据黄河淤积的情况,需要挖掘比引河工程量小些的抽沟或沟线,当然,并非六百余里全要兴工,但两省都要动工是必然的。林则徐与河道上的人也有个粗略估计,河南境内,引河大约要有九千多丈左右;抽沟、沟线长度大约是引河的两倍。引河口宽六十余丈,深约三丈,土工量相当大。
王鼎说:“少穆,你也知道,英夷在南边寻衅,朝廷军费一项开支已达数百万两,真正是捉襟见肘。黄河大工,能省则省。临来之前,我让户部查过黄河大工经费情况,乾隆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岗决口用银两千万两;嘉庆十三、十四年,南河修堤堵口费用四千多万两;嘉庆二十四年,黄河马营决口,耗银一千二百万两;嘉庆二十五年仪封决口,耗银四百七十余万两。我有个打算,远处的不说,就依最近的大工为依据,马营大工耗银一千二百万两,太过浪费;仪封大工耗银四百七十万两,较为撙节。河工上贪污浮冒已成积习,动辄上千万两银子,实际用于工程的十不及二三。我以为此次大工,按仪工四百七十万两奏请朝廷拨款。”
林则徐连忙说:“相国,这个概算实在太少,恐怕不敷应用。当年仪封决口不到二百丈,引河、抽沟工程量更是少之又少,拿此预算比照的话,恐怕要增三分之一也不止。”
如果比仪封工程增加三分之一,那就是六百余万两。
王鼎说:“少穆,仪封工程,中间也有不少虚头,我管户部多年,十分清楚。把这部分水分挤掉,五百万两以内拿下这次大工,也不是没有可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管户部多年,国家财政那真正是捉襟见肘。我临来前,皇上召我独对。他撩起龙袍对我说,王鼎啊,你看我这堂堂天朝皇上,穿的龙袍也打了补丁。不是打个补丁的钱也没有,我是想表率天下,倡导节俭的风气。你有铁算盘之称,你到南边去督办大工,好好尽心,给朕省点银子。朝廷实在是难啊。少穆,皇上对臣子说出这样的话,与寻常百姓向人乞讨有何两样?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我对皇上说,我一定鸡蛋里省出骨头来。皇上说,我信你。”
话说到这份上,林则徐心里酸得很。他说:“相国,我理解您的苦心。只是户部向来打折扣,能拨给十之六七就不错,如果报四百六七十万,只怕四百万两也拨不下来,那缺口可真就太大了。”
王鼎笑笑说:“你别忘了,我是管户部的,他们不会与我讨价还价,而且我临走时也跟皇上说过,我用一分报一分,绝不虚冒。还有,我上奏的时候,笔下会留点余地的。”
林则徐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感觉,王相国对工程的浩繁费用和河工上贪墨银子的手段太过小瞧。
王鼎说:“少穆,大工马上开始,我有个想法,我和慧通政他们,天天蹲到大堤上去,现场督促。朱河帅到后,让他负责督修大坝。你呢,是治河的行家,又是人人皆知清正不阿,你襄办文案,其实就是帮我拿总;另外,我再给一项任务,总理核算大工费用。我的打算,就是这四百七十万两银子拿下工程,你拿出所有手段,给我鸡蛋里省出骨头来。”
林则徐连忙说:“相国,我是戴罪效力,如何能承担如此重任!万万不可,只负责文案,我还能勉强。”
王鼎说:“少穆,文案何劳你费神,只要粗通文字就能胜任。我以襄办文案之名把你调来,你还真以为让你总办文案,你不必推辞。”
林则徐只好硬着头皮应下来。既然答应了,就要设法在撙节支出上先就大的方面提出几条建议。一是在大工埽料上力求节省。这次大工埽料需求量极大,至少需要八千垛,每垛五万斤计,大约四万万斤。豫南被淹,豫北大旱,单靠附近州县难以供应,建议奏请朝廷命河南及鲁西南部分县都要承担供应任务。为了杜绝河道上贪墨,届时由各县委派人员前来交割,不用河道上派人四处购买。二是引河工程上要撙节。引河需要挖掘大量土方,河道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土性疏松,容易挖掘;有的是胶泥,板硬难掘;有的还会挖出泉水来,给施工带来难度,核算工值出入极大。另外沿河还有痞棍会强揽工程,文弱者无可应付。林则徐建议,引河工程用武员不用文员,并由钦差派出武员前往监督弹压,一则可以监督浮冒工值,二则可防痞棍刁难。林则徐建议王鼎奏请,可就近调兵一营,直接归钦差调遣。三是趁秋汛即将结束,组织两岸灾民尽参加引河工程,赶造挑水坝,这样以工代赈,既能给灾民一条活路,又能压减一笔开支。最好在寒露前能够开工,因为一到冬天,天寒地冻,施工不易,工费会大幅增支。对林则徐这三条建议,王鼎一概照准。
王鼎又与副钦差慧成等人进行了认真商议,过了两天,在钦差行辕召集上至巡抚牛鉴,下至候补知县等近百人的会议,对整个大工进行分工。东西两坝,分别设总局,总局以下,又设文案、银库、正料厂、杂料厂、蜡烛局,总局的掌局都是由道台、知府出任,以下各厂局则从知州、知县、候补知县以至未入流官员中选任,人员构成则有河工上的,也有地方官员,还有在籍士绅。引河工程也专门进行了分工,有勘估、总催、分催等职司,也是从道台、知府到未入官员都有。在河帅朱襄到来前,巡抚牛鉴则统领两局。
王鼎提出,西坝工程量大,必须赶在寒露也就是九月初九日前开工;东坝则视埽料征购情况而定。要开工,埽料最为关键。开封附近河上备埽千余垛,可尽先运来用。但区区一千垛,远远不够,必须赶紧收购,否则到时候埽料不继,停工待料,那就要延长工期。王鼎的意思,当年仪封河工,埽料每垛用银一百八十两,本次征购就以此为上限。豫东南是灾区指望不上了,豫西北三十六州县分别采买埽料,离开封百里内者,每垛发银一百六十两,远者递加,但最高者不能超过一百八十两。已经给各州县下达了征购任务,由各州县专门委员负责押送到大工现场。
各县送埽料前来,必须现银交割;一旦开工,工夫们的工值也必须及时发放,一有拖欠,工夫们就会停工闹事,这已经是惯例。而且天气渐凉,转眼就将冰天雪地,在水里施工,是件苦差事,也的确不能拖欠工钱。王鼎预计,朝廷的拨款大约十月初可到,如果有五十万两银子就能应付过九月。他的办法是先借,已经安排河南布政使鄂顺安想办法。鄂顺安的办法,是藩库里先挪借十万两,开封府负责让城内八家典铺先把旧存官银十五万两交出来,八大钱庄则筹借给官府二十万两,近省各邑殷实富户再借十几万两。西坝开工前筹起五十万两问题不大。
隔天奉到上谕,王鼎所请一概照准,由广储司拨银二百万两,山东、山西、淮关等应解部款二百余万两,直接解到祥符河工,另七十万两户部拟于一月内设法筹解。
果然是一点折扣也没打!
王鼎很高兴,对林则徐说:“少穆,咱们放心开始大工就是。”
九月初七早晨,王鼎和牛鉴率领钦差行辕、巡抚衙门、河道上的人员来到西坝开工现场,主持开工仪式。大堤上已经设了供案,上供三牲等祭品,由王鼎率领,祭拜河神。祭罢,再到大堤边,这里已经备好十几筐土,王鼎和牛鉴两人共抬一筐,倒到河里。其他官员也各自结对,向河里倒土。此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象征着河工正式破土。
按照预定的计划,从东西两侧各修大坝,因为西坝工程量大,先行开工。坝基就接在大堤上,这里是新坝的根基,将来又要作为存料、配料、加工、调度的场地,因此需要修得特别宽阔、牢固。大堤决口后,堤内漫灌的河水已经从决口排泄出去一部分,大堤附近的河滩只有坑洼处存有积水。河工们下到滩上,沿着坝基方向挖出新淤的稀泥,并填平坑洼,夯筑结实,然后堆进土石,层层夯筑。大堤上数百辆小推车来来往往,坝基上也有百余人在推平、夯筑,而堤外人更多,整个工地不下千余人,非常热闹。
坝基土工三天后完成,接下的工程需要在数米深的水中进行,就需要捆厢船进行埽工作业,“进占”筑堤了。
所谓埽工,就是以草、柳、庄稼秸秆等薪柴配以土石,用绳桩等捆扎、固定,构成抢险堵口的材料。黄河上以埽工抢险堵口,历史很悠久,有的说起源于先秦时期,有的说始自汉代。历代都有所革新,到了清代,用船捆扎埽工,这船就叫捆厢船。其方法当然是颇为复杂,需要专业人员来完成。简单来说,就是把捆厢船停在坝基附近,在坝基上打许多木桩,桩上拴绳,绳的另一端拴在捆厢船上,然后在绳上铺一层秸料,加一层土石,埽绳随加随松,最后埽工沉入水底,再在顶面及两侧堆加土石,于是新坝完成。然后再在新坝上打桩、拴绳,重复前面的过程,一节一节向合龙口筑坝,一节称为一占,因为水中筑坝不容易,尤其是接近合龙时,水流湍急,更是困难重重,因此河工上称这种堵口办法为“进占”。
“进占”之前,先要固定捆厢船。这次决口水量很大,坝体必须宽厚结实,因此选用了黄河上最大的船——长近八丈的木船改造而成,把前后桅杆、船舵都拆去,船舱又专门趁上木板加固,再在船上固定一根纵贯船头、船尾的木头——龙骨,用以在上面缠拴绳索。备好的捆厢船被拉到坝基跟前,然后在上下游各停一艘船。上游的船称为提脑船,下游的称为揪艄船,两船都抛下数千斤的铁猫,固定在水中。然后提脑船上的绳索拉住捆厢船的船头,揪艄船上的绳索拉住捆厢船的船尾,使捆厢船得以固定,避免上下游动。
捆厢船固定后,将固定在坝基四根木桩上的四股大绳分别绕过船底,再拉出水来,系到龙骨上,这样便将捆厢船与坝基固定在一起,避免向外漂移。然后再将十几股绳索一头拴牢在坝基木桩上,一头直接系在龙骨上,下垂到水面,在各股绳之间,再以细一些的绳索编连,形成网状。捆厢船边上,每隔半米左右站立一人,各持扎杆一根,竖立水中。这时船上升起红旗——夜里则升红灯,这是上料的信号,坝上供料人将一捆捆秸秆铺到绳上,一直铺到与坝平齐。红旗降下,表示停止供料。指挥则站到捆厢船龙骨上,手持红旗负责指挥;铺料的人分为两排,站到料堆上,随着指挥的旗号,一齐跳跃,秸秆不断压实,船上管绳的人则配合着慢慢放松绳索,船慢慢外移,秸料慢慢向前铺开、摊薄。这叫“跳埽”。“跳埽”是有危险的,力度太大,埽料突然向前滚翻,“跳埽”的人就会掉到水里。林则徐和王鼎等人站在坝基上,紧张地盯着他们,心提到嗓子眼。好在他们都还算熟练,没出问题。
反复“跳埽”几次,船离开坝体已经五丈左右,就停止松绳,船固定下来,铺埽的人站到埽面上,对埽料进行整理、找平,然后再以绳索编织,固定埽料,并打下数排尖桩,以备埽体最后沉到底时扎进河床里,起到固定作用。然后在埽面上铺上一层薄土,再在上面铺秸料,铺到一定厚度,再铺一层土。越往上,堆土越厚。同时,每铺一层料,要在埽体上打入多种组合的木桩,并用绳索固定,以免埽体移动、翻滚。一直到埽体沉到水底,并出水五六尺左右,一占才算告成,同时在迎水面和背水面堆加沙袋、土石,对埽体进行加固。林则徐陪着王鼎等人,天天盯在坝基上,直到一占完全完成。王鼎说:“真是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林则徐告诉他,现在还未靠近河水主流,进占比较容易,等进了河水主流,水又深又急,那时候必须经验十分丰富的埽工才能胜任,尤其是合龙的时候,险象环生,非有南河熟手主持不可。
大清国设有三个河道总督,南河总督,东河总督,北河总督。北河总督负责永定河、海河的河务,例有直隶总督兼署。实际上称得上专业治河机构的只有南河总督和东河总督衙门。两者相比,南河才能称得起真正专业。或许是民风不同,北方人对粗老笨重的力气活不怵头,而对心灵手巧、眼疾手快的技术活总不比江南人。表现在治河上,举凡下桩、捆厢、进占等技术,东河河工总不及南河,尤其是抢堵决口这种急难险巧的工程,非有南河大批熟手在工不可。不知始自何时,东河出险,例请南河派人前来,不仅要派技术熟手,就连河工也要派数百人来。王鼎已经向朝廷奏请,并写信让新任河督朱襄一同带来。
王鼎说:“我已经写信催促朱河帅,他正在星夜兼程赶来。他是从浙江前来,路途遥远,急也没用。”
西坝“进占”开始后,大堤上下一片繁忙。堤下有正料厂,将高粱秸、柳梢、黄草等按比例打好捆;将土、石、砖等分派民夫随时运到坝上。杂料厂有木工作,专门制作大小长短不一的各类木桩以及齐板、拦板、撑杆、扎杆、叉把、手硪等各种作埽工具;有绳缆作,专门制作底勾绳、占绳、过肚绳、揪头绳等,按材料分则有草绳、棕绳、苧麻绳、茼麻绳、竹缆、铁丝缆等;有编修作,专门负责编筐篓、修理小推车等。此外还有伙房,专门烧水,炒菜,做饭。坝基上则堆满各种备料,各有专人负责。王鼎天不亮就到坝上去,晚上掌灯了才下坝。他从五月底背上就生疮,三个多月了一直没好,身体很虚。他乘肩舆上坝,摆下几个马扎,就坐在马扎上与慧成、张亮基、林则徐等人议事。有时下雨,他也不肯下坝,于是就在坝上搭了一个席棚,他实在累得坐不住了,就到席棚里躺一躺。
祥符上下游的埽料陆续运到,同时附近州县新购之埽也有的已经运到,大堤上下十分热闹。王鼎让林则徐负责验收,对他说:“少穆,埽料是大工支出的最大项,如果收埽这一关把不严,虚靡帑银,所关不轻。我知道你对这里面的弊端十分清楚,你现在挑几个人,帮着你验收埽料,查出蒙混浮冒的,坚决严办。”
林则徐说:“相国,秸料是河工第一要物,也是河工第一弊端,堆料积弊,花样百出,非有掌实柄者不能根绝,我只怕难负其任。”
林则徐并非推诿,清查埽垛积弊,是件得罪人的活,何况利益攸关,他一个无兵无权的“效力”戍臣,如何能够办得了?
王鼎说:“少穆,推诿怕事可不是你的性格。我把你调来,就是指望你这行家里手,能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这次大工,既要办理扎实,更要力杜虚靡,我是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的。”
林则徐说:“相国,查验出弊端不难,关键是如何惩办。”
王鼎明白林则徐的难处,对牛鉴说:“镜堂,查勘的事由少穆负责,惩办的事则由你来办理。关键时候,你可以请出王命旗牌,先斩后奏。总之,要让那些敢在埽料上做手脚的胆寒才行。不然,这可是个无底洞,我在皇上面前立下的军令状可就打了折扣。”
牛鉴说:“放心吧相国,让少穆瞪起眼来查验,我狠下心来惩办。”
牛鉴从巡抚衙门选派了几个人,跟着林则徐查验埽垛。埽料有的堆在大堤上,有的堆在堤下。堆在堤上的,称为门垛或头垛,是门面货,其中弊端少;堆在堤下的,称为底厂;离堤远堆在滩涂上的,则为滩垛。历来河官检验埽垛,往往沿着大堤,查验门垛走走过场,至于底厂、滩垛,则很少查勘,因此弊端百出,最易蒙混。收埽料是按斤付款,河工上则是按垛验收支付,蒙混的手段便在堆料时玩花样。按照要求,堆垛必须层层堆叠,高过一尺后,周围用木板打紧,然后再堆。最普遍的作弊手段,就是横一层竖一层,虚空排架,甚至有些垛四周结实,中间虚空,行话为“井垛”;有的新旧混垛,名为“并垛”;还有的以新盖旧,名为“戴帽”……结果四垛的料却堆出五垛来,河道按五垛付款,这多出的一垛料钱,便被层层分肥了。
林则徐当了三个月的东河总督,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到河南查验埽垛,对其中的积弊摸得门清。他知道王鼎办事认真,而且任由收埽的人蒙混,也不是他的个性。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带着四五个人,挨次详查,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对虚冒太甚的两垛,林则徐竟然安排人按束称斤。每垛应当五万斤左右,而林则徐称斤的两垛,仅三万斤有余。牛鉴当场宣布撤去负有责任的兰仪厅同知之职,并让具体经手人赔补两万斤。一天下来,负责埽垛的都心惊胆战,私下里骂声不绝。
当天夜里,滩厂埽垛突然失火,当夜又有大风,火借风势,延烧数十垛,大火映红天边,连开封城的狗也狂吠不止。因为大工所需人夫极多,所需物料又杂,因此大堤附近俨然市集。大火一起,不法之徒趁机抢掠,方圆数里一片混乱。后来牛鉴派抚标中军率二百余人赶往弹压才平息下去。
林则徐连夜赶到失火现场,着人清点,过火埽垛二十七垛,完全被烧毁的有十三垛。天刚亮,王鼎和牛鉴一同到了现场,问林则徐什么情况,林则徐说:“情形十分可疑。该厂在南岸之南,地居底路,本属空旷,不与民居相连,四面挖有沟壕,前设栅门,专人值守,足以防犯。并且专派兵丁三名看守,又有汛兵往来防护,怎么可能轻易失火?”
王鼎问:“那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纵火?”
“十有八九。”林则徐说,“当年我任职东河查验埽垛时,也遇到失火的情形。后来严加审讯,原来是他们埽垛有弊,为了掩饰不惜纵火焚烧灭迹。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我们不再严加查验。”
王鼎气得脸色铁青:“真是可恨至极!他们为一己私利竟出此下三烂手段!这是公然挑衅,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少穆,你就说吧,该怎么办?”
“让有关员弁赔补,这是河道惯例。对相关人员交官审讯,也是必不可少。”林则徐说,“这还不够,必须请出王命旗牌。”
这把王鼎和牛鉴都吓了一跳,王鼎问:“少穆,你的意思是要杀人立威?罪不至此吧?”
林则徐说:“当然罪不至此。相国你知道,河道上的官员花样百出,几乎无人不贪,他们不缺银子。对他们来说,赔补点银子根本不算什么,而且过后众人会帮他们凑银子。而审讯的结果,往往查不出放火之人或者以不慎失火结案。他们敢于如此嚣张,原因正在于此。他们也不怕上宪心知肚明,甚至希望上宪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把我们吓退。我们不但不能退,而且必须以霹雳手段把他们镇住,不然埽垛之弊不能剔除,相国撙节靡费的设想将化为泡影。”
王鼎说:“割除弊端是必须的,可是,毕竟人命关天。”
林则徐说:“杀人是真,但未必真杀此辈。”
“此辈不缺钱,但惜命。动了真章,他们也不敢不收敛。”林则徐的意思,把有关人员交官严讯,同时宣布处死一两人,请出王命旗牌,到大堤上宣布罪状,现场斩决。至于所斩之人,可从开封府死牢里提取罪大恶极已判斩决的囚犯。
牛鉴说:“哦,明白了,你这叫偷梁换柱,杀鸡赅猴。”
王鼎笑道:“想不到堂堂林少穆,也会使诈。”
林则徐说:“对付奸诈之徒,当然无法尽用君子手段。相国,此事只有你和牛抚台知道实情,咱们是要演一场戏,可不能演砸了。”
王鼎说:“好说,咱就以大堤当舞台,陪着你们演一场好戏。”
开封知府邹鸣鹤连夜审讯,巡抚衙门专门派人送去王命旗牌,说如果有人拒不认罪,可请王命先斩后奏。结果不出两天就审理清楚,授意的是一位通判,被革职,并负责赔补损失;负责分汛的千总被降为把总;负责驻守的把总及两位兵丁被判充军,放火的兵丁斩立决。
失火案的宣判与执刑在大堤上进行,由开封知府宣布审理结果,由巡抚牛鉴请出王命旗牌,当场斩决纵火的兵丁。兵丁看来受了大刑,双腿膝盖似乎已经被打断,根本站不住。脸上满是血污,披头散发,垂头丧气。人被推到决口的大堤边,一刀斩讫,头颅落进水中,被冲得无影无踪。同时,钦差行辕贴出告示,再有敢上下其手,贪墨不法,阻碍大工者,严惩不贷。
邹鸣鹤又建议,新到埽料由开封及附近州县的士绅组成收埽局,下设几个分局,分片收购,并于当天在埽厂公告,收某县多少斤,价值几何,总计几何,每日入账,必须由各县派来的委员签字。
王鼎对这个建议很赞赏,立即采纳。
埽垛之弊几乎是一扫而空,河道上的人不能插手收埽,不免愤愤不平,深恨林则徐、邹鸣鹤多事。然而,整个工地上,王鼎德高望重,巡抚又是言听计从,林则徐在河南百姓中口碑又好,河道上的人再有怨言,也不敢明目张胆。西坝的进展也很顺利,照此进度,腊月中旬合龙当有把握,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
大家配合得正融洽,却忽然有两道上谕飞递到大堤上,第一道是:“以河南巡抚牛鉴署两江总督。河南布政使鄂顺安署河南巡抚。”第二道是:“又谕:本日已明降谕旨,将牛鉴补授两江总督,并令迅速驰驿前往,毋庸来京请训。江苏各海口防堵事宜,亟须筹办,该督接奉此旨后,务即迅速起程,驰往该省亲历各处海口,相度情形,悉心筹划,将一切防剿事宜,赶紧妥为办理,务使处处有备,不致临事周章,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王鼎说:“镜堂,恭喜恭喜,两江一职仅次直隶,要是从财赋上来说,两江又重于直督,历来是由皇上简派重臣能员出任,可见你简在帝心。”
牛鉴却高兴不起来:“老相国,如今英夷在沿海寻衅,我从未在军务上历练,心里空慌得很。”
林则徐有种不祥的预感,说:“裕鲁珊总督两江,奉钦命在浙东督办军务。这两江总督出缺……”
王鼎说:“裕鲁珊屡屡上折,说浙江防务固若金汤,应该不会出事。也许皇上考虑让他一心军务,因此让镜堂署理两江。”
牛鉴说:“对,对,等裕制军回任两江,我也许就又回到河南了。”
王鼎说:“镜堂,上谕让你不必进京请训,迅速起程,驰往海口,可见事机紧迫。你赶紧回开封,还要办理交接。”
像这种情况,接到旨后最迟后天就应上路,的确是千头万绪。他收拾一下立刻回开封,临走时对林则徐说:“少穆,我对沿海知之甚少,尤其是海防更是陌生。这些日子一直忙着救灾,没来得及向你请教,现在时间又这样紧,你对海疆、海防必有高见,还请百忙中赐我一稿,我到两江好依样画葫芦。”
林则徐真是有很多想法,也正借此机会梳理一下,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掌灯时分林则徐才陪王鼎下堤,回到关帝庙吃过晚饭,又议明天该办的事项,等回到住处,已经十点多了。他又累又困,但还不能睡,他要把给牛鉴的建议写下来。今年自从离开广东,他一直在反思,认为对付英夷,必须尽快建一支外洋水师,仿造英夷火炮。他在镇江与魏源夜谈时说起过这一点,如今牛鉴特意征求意见,如果这一条能得重视,在两江扎实办理,对付英夷便能有几分把握——
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而为之防,不唯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在前岁粤东藩维未破,原只需于要口严断接济,彼即有坐困之形,冀其就我范围。今所向无所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所损失,何所忌惮?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比见征调频仍,鄙意以为非徒无益,盖远调之军筋力已疲,久戍则情志愈惰,加以传闻恐吓,均已魂不附身,而况不习水土,不识道途,不过因在营食粮,难辞调遣,安有斗志?是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而朝廷例费之多,各营津贴之苦,沿途供应之疲,民间车马之累,言之可胜太息乎?大抵民无不畏兵,而兵无不畏贼,事势如此。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夷炮。忆去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倘彼时得以制办,今秋浙中尚可资以为用。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不可缺,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
深知阁下耿耿丹忱,同仇敌忾,兹谨率摅胸臆以陈,以供酌采。附录去岁训练水勇数条,乞斧削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