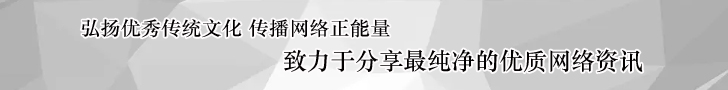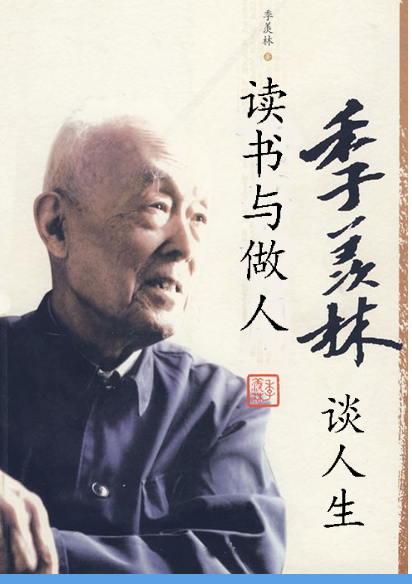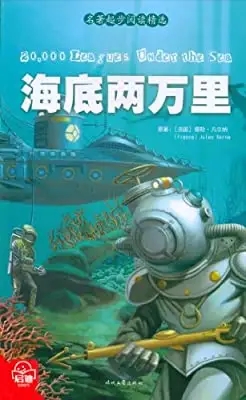三、取官商督办 大兴民用业
除继续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李鸿章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郭嵩焘再度出山,任福建按察使。其时清廷正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将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希望借此强大起来,恐怕只会让自己走向灭亡。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大力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而李鸿章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家形势,也发现“国家必须先富起来,而后才能强大,尤其必须先让老百姓富起来,而后国家的根基才能更加稳固”。只有国家富裕了,才有能力求强,以求富来维持军工业,这是李鸿章在十几年洋务运动中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的提升。
此后,“必先富而后能强”成为洋务派的基本主张。
李鸿章一边大力发展军工工业,一边着手创建民用企业。他说:“欲自强必须有资金,欲疏通饷源不如振兴商务。而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贫困,西洋方千里、数百里的国家,每年的财赋收入动辄数万万,无非来源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审时度势,如果不早图变革,选择其中重要的方面逐渐仿行,那么,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最终没有不受其害的。”其后,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多个行业。
为了求强而求富,李鸿章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及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及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当时国内已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在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长年失修,淤塞不通,清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由海路运输。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拟开始筹办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的基本设想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和载客;有战事时则可输送军火。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与外国的船运相抗衡。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为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岁月,每逢年底有股东分红。一些经济学者对当时招商局的财务情况做过详细的分析,认为招商局是一个有西方资本企业管理模式的股份制公司。招商局成立之初仅有轮船3艘,而其后展开的客运业务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的一半运量,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兼并旗昌公司产业后,招商局共拥有轮船33艘,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年收入平均约为200万两白银,年净利为30万两白银。
为了使“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才不会受制于人,同时还避免利润外流”,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了煤矿开采业。光绪二年(1876年),他派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源,并于翌年批准唐廷枢提出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为了争取地方官吏的配合,李鸿章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光绪四年(1878年),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先是官督商办。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委托徐润和吴炽昌为会办,以代替他调走的黎兆棠和病逝的丁寿昌。该局起初以开采煤、铁为主,兼炼钢铁,后因经费和技术问题,遂停止炼铁,专采煤矿。资本从80万两银增至150万两。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该局日产煤2000吨。开平煤矿是洋务派创办的采矿业中业绩最佳的大矿。
漠河金矿是李鸿章等奉旨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另一大型企业。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黑龙江,与沙俄毗邻。清廷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开采漠河金矿,命令李鸿章与黑龙江将军恭堂遴选熟悉矿务的精干人员,前往矿区勘察。翌年,李鸿章奏准由道员李金镛总办漠河金矿,“除重大事件应禀商黑龙江将军酌夺外,其余一切由该员相机行事,以专责成”。漠河金矿的开办资本,由官款垫借白银13万两,募集商股不到3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漠河金矿正式开采。
李鸿章最具远见的莫过于开设铁路和电报。
最初,当洋人想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时,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认为“电报的设施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起初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他就曾经断言:电报铁路“有利于外国,而对我大清国则极为有害”。但到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改变了态度,历陈“电报、铁路必应仿设”。光绪五年(1879年),鉴于“各国以至上海无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唯独中国文书还在依赖驿马传递,虽日行六百里加急,但速度仍远远落后于外国的电报”,他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于是饬令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线试设电报主干线。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又奏请接修天津经镇江至上海的电报线,并于津沪电报线路铺设期间,在天津设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
光绪八年(1882年),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商股接办贯穿苏、浙、闽、粤四省电报线路,于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峻工,之后电报局由天津迁到上海,以盛宣怀为督办,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为会办。与此同时,电报局继续招商集股,架设了津京线、长江线、桂滇线、陕甘线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鸿章奏报朝廷说:“臣查中国陆路电线创自光绪六年(1880年),经营10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19世纪70年代,沿海再度吃紧。在晚清文武大臣中,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李鸿章,其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国防。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廷组织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战略,其中格外强调铁路的军事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日行千数百里,如此统帅便不至于误事……”而反对派的理由则是:“开铁路容易使山川之灵不安,导致干旱和洪涝。”
尽管李鸿章的倡议引来一片反对之声,但他并不甘心,他的聪明与狡猾,就在于他懂得阳奉阴违的艺术。为了修建铁路,他一面批驳顽固分子的反对言论,一面授意唐廷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即在开平煤矿修筑至唐山胥各庄之间的铁路,以便运煤。
光绪二年(1886年),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䜣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详细商议修建铁路的办法。此时的奕䜣位高权重,但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建铁路,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开平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只有这样,这件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这一思路可行,加上在唐胥铁路的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距离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为避免遭到朝臣非议,他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驴马拖载,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光绪六年(1880年),唐胥铁路竣工。李鸿章自然不会满足于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一直伺机争取更进一步。同年,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开平矿务局以方便运煤为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10千米延长到约40千米,唐胥铁路随即改称唐芦铁路。光绪七年(1881年),唐芦铁路通车,终于用上了机头。这台由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汽机车头,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头。但通车没多久,由于“机车直驶,震动了东陵,而且喷出黑烟,有伤庄稼”,机头被下令禁止使用,运煤的车皮再次使用驴马拖载,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把铁路说成“马路”。他迂回前进,总想把马路变成真正的铁路。很快,他又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由奕䜣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铁路是为了调兵运送军火,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为130千米左右。从修唐胥铁路到延长至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至此,李鸿章信心倍增,又上奏要求朝廷正式批准他的铁路修建计划,没想到这次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因对醇亲王有所顾忌,才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地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真是忍无可忍!反对声就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劾的奏章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修建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这时,李鸿章耍了个小心眼,决定设法送慈禧一个小礼物,让她亲自见识一下火车的魅力。光绪十四年(1888年),古老的皇宫西苑,从中南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赞助的1500米长的微型铁路,与之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和6节小车厢。这个可以快速行进的“玩具”,成了皇亲国戚们在深宫后院的游览花车,大开眼界的慈禧转而明确支持修建铁路,长达10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是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而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条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厌烦了宫闱中时有机车声响,又将机车头驱动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缓缓滑行。这成为晚清末年又一幕荒诞滑稽的插曲。
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铁路局。第二年,关东铁路动工修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铺轨到山海关,光绪二十年(1894年)修路到中后所。这段铁路的经费全部由清廷拨款,故称为“官路”。
李鸿章兴办的民用企业,除了北洋铁路局是官办的以外,其余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他认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是为了“收回中国经济上的利益。事关重大,有益于国计民生,所以必须由官府扶持并酌借官银以弥补商力的不足”。为此,他想方设法为官督商办企业借款缓息。
早在接任两江总督之初,李鸿章便打定主意,力争署期内在金陵也办上一两个实业,其中之一就是创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当时洋货行销中国,日益兴盛,其中尤以洋布为最。但大清百姓只知洋布纹路细腻、厚薄均匀,却不知是如何织出来的。李鸿章也是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以后,才从容闳、唐国华等人的口中知道详情。他决意引进织布的机器,办成一座工厂,打破洋商垄断洋布的局面。何况江南茧业最为发达,将工厂建在金陵,收购棉花、茧丝,不但免去许多转运花费,而且还可随用随购,用不着大量囤积。
光绪二年(1876年)初,李鸿章派魏纶先具体承办织布事宜。魏纶先前往上海筹议此事,后因经费筹措困难,计划被搁置下来。
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向李鸿章和沈葆桢提出了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的计划,并亲自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一计划十分支持。彭汝琮返回上海后,委派郑观应为会办局务,立即进行建厂的筹备工作。
郑观应(1842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我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郑观应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郑观应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
郑观应任会办局务期间,由于和彭汝琮意见不合,筹办工作极为缓慢,不久,二人相继离开纺织局。
光绪六年(1880年)春,机器织布局由戴恒主持,戴恒又邀请郑观应入局,在他们的努力下,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同年秋,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宣告成立。由于集资顺利,郑观应等立即开始了建厂的工作,并委托美籍工程师丹科购买机器。机器于光绪九年(1883年)运抵上海,其中包括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设备。
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过程中,上海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股票价格大跌,上海机器织布局出现严重亏损,郑观应难以维持,只得离职,上海机器织布局改由龚寿图、龚彝图兄弟接管。但是,龚氏兄弟也难以重振局面,李鸿章又派马建忠主持工作。在马氏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上海机器织布局又改由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主持。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历经波折,终于竣工,于次年开始投产,年产棉布400万码,棉纱100万磅。
就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营顺利,并获得丰厚利润之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清花厂突然发生火灾,厂房和机器大部分毁于大火,估计损失不下70余万两白银。上海机器织布局成达数年之久而毁于一旦。李鸿章很不甘心,派盛宣怀前往上海处理善后事宜,并另行筹集资本,在旧址设立新厂。
盛宣怀(1844年—1916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
盛宣怀经过考察,提出了新的建厂方案。李鸿章批准了这一方案,同时将厂名定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光绪二十年(1894年),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开始部分投产。但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外国资本到华投资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华盛机器纺织总厂连年亏损,无法维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盛宣怀将该厂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总厂,实际上成为盛氏的家族产业,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的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从此结束。
李鸿章这人,凡事都爱沾个洋气儿,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他创办西医院。光绪四年(1878年)冬,他的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因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不知吃了多少服中药,但病就是不见好转。李鸿章无奈,只得请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6天中,马根济采用“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救了李鸿章夫人的性命。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由兴趣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官僚士绅的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根济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根济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6000两白银,加上他亲自捐赠的4000两,共计1万两白银。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据《天津通志》记载,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鸿章实际操控的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及上海机器织布局,另外与他有联系的还有平泉铜矿、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银铅矿、华盛纺织总厂、上海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等。民用、运输企业共有27家,其中李鸿章经办的为12家,占近一半;所用经费总额为2960万两白银,李鸿章所办公司占到44.6%。
洋务运动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了。
四、反思旧教育 培养留学生
在洋务派推动洋务运动的同时,西学东渐,西式教育迅速在封闭的大清国内逐步兴起。李鸿章在大力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还参与了种种文化教育活动,多方面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积极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近代人才。
同治二年(1863年),应幕僚冯桂芬所请,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外国语言文学文字学馆,随即改称上海广方言馆,兼聘洋人为教习,主要招收14岁以下、禀赋端庄沉静的幼童,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兼习西方人所擅长的测算之学、格物之学、制器尚象之法,以期“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可以逐渐通晓”。该馆学制为三年,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军工科技人才。
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又开设了天文算学馆。同治八年(1869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大本营。李鸿章在里面附设了翻译馆,招收15至20岁的学生入学,除了外语,又增设算学、舆地等学科,学制改为4年。
我们知道,李鸿章是一个历经科举考试严格训练的封建士大夫,他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在他心中埋下了较深的根基。然而,随着时势的推移,尤其是对西方文化逐渐了解和接触,对比中国落后受辱的严酷现实,李鸿章对八股取士制度从怀疑发展到厌恶。而在当时,随着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举办,李鸿章认识到要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的阶段,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
李鸿章首先对旧科举提出了质疑和部分改良。他试图改变传统教育以四书五经选择人才的模式,将科技、实用知识引入学校,培养专科人才。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自然受到了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但李鸿章并未就此停止呼吁,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一道奏议中写道:电报、军械等事物,已经极大地改变世界,而国内既无钱也无人可以应对,实在堪忧。因此,他对借鉴西方的技术与理念更加重视,以至于后来的史料称,李鸿章一旦听说欧美推出了新的武器,必千方百计购入,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他呼吁凡有海防的省份,均应设立“洋学局”,选择通晓时务之人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学数门,这些都关系到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本”。将各种略通一二的人才选收入局,并以博学与精通的洋人作为其师友,按照所学深浅,酌情给予薪水,待到研究得精通明了,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补充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再区分文武,照军中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于勤奋而终于懈怠,立予罢斥。由此可见,李鸿章的这一主张,另开洋务进取一格,目的在于通过“洋学局”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才,使之“与正途出身无异”。
李鸿章试图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学兼汉宋、道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成分,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不过,李鸿章的认识和实践是脱节的。甲午战争之后,他曾反思说:“论者都知道时文试帖没有用,又不敢倡言废科举,总想调停其间,于是艺科算学之说,迭见条陈。”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既不敢倡言废科举,更不敢奏请易官制,只好一面设法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一面力所能及地扩充西学。
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李鸿章的倡导下,上海格致书院成立,随即由近代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时任英国驻沪总领事麦华佗改建为格致中学。时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传授“格致之学”的学堂成为我国近代最早开办的中西合办、最先传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的新型学堂之一。
在东西方教育体系的对比中,李鸿章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的方法,条理精严”,而东方的就太显呆板,一成不变,刻板的八股文仍旧沿袭所谓的儒学思想,在实质作用上是无法与西方教育相比的。
在其后的办学实践中,李鸿章发现,朝廷任官重科甲正途而直接影响着学堂学生的来源和质量。他说:“除学堂、练船外,实在没有可资造就将才的地方。唯朝廷似乎不太重视此事,部臣又以一般的功绩而苛求之,世家有志上进者都不肯就学。”他为此忧心忡忡,不得不趋就现实,力图通过为学堂人员争取“与正途并重”或“由科甲进身”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光绪六年(1880年)底,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天津水师学堂,诏准。
天津水师学堂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定条例和计划,是清王朝首家培养海军人才的专门学堂。该学堂筹建伊始,李鸿章力保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海军军官担任教练,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支销,分设驾驶、管轮两科。驾驶科专习管驾轮船,管轮科专习管理轮机。学员兼习英文、地舆、算学、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力学、化学等,功课与英国海军学校完全一致。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应诏陈言,指出编练水师必须“选将取才”,建议对学堂人员“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严格考核,对贪惰者立予罢斥”。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决定对“求才之格”“量为推广”。李鸿章随即上疏,为学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是年,御史陈绣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奕等人认为“试士之例不可轻易变更,而求才之格则可量为推广”,建议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准生监报考算学,除正场仍试以四书、经文、诗策外,其经古一场另出算学题目,考生若能通晓算法,即报送总理衙门复勘注册,遇乡试之年,考生亲赴总理衙门,“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进行考察”,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如果人数在20名以上,于乡试卷面统一加上“算学”字样,与通场士子一起考试,不另出算学题目。试卷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20名于额外取中一名,“文理清通即为合格”。但卷数虽多,中试人数不得超过3名,以作为限制。至于会试,则因从来没有另编字号的做法,所以凡算学中试的举人,“仍归大号,与各该省士子合试,凭文取中”。在他们看来,“如此一来,在搜求技术人才之时,仍不改科举取士之法,也算是鼓励人才的途径之一”。
奕䜣等人提出的方针办法,得到了慈禧的批准。李鸿章企图为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及教习人员争取科甲正途出身,特地上疏说:“创设学堂,虽然是为了造就将才,但都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其中也有文理清通而志向远大者。倘若他日得以由科甲进身,则文武兼备,未尝不可成为抵御外侮、捍卫城池之人选。……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乡试之年,除各省士子兼通算学者,由本省学臣考试咨送外,所有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及教习人员,届时就近由臣这里遴选精通文理的人员,开单咨送总理衙门,听候考试录送,一体乡试,以资鼓励并开拓举用人才的途径。如幸而会试得中,仍归学堂及水师陆军调用,以收实效。”此议奉旨允准。于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及学生得以和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
这次乡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西学和中学同考,把八股取士的藩篱冲破了一个缺口,从而成为戊戌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
与开办学堂之事相比,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无疑是又一个教育新举措。曾国藩、李鸿章及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共同促成了这个古老国家第一次派出留学生赴美学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个叫布朗的美国传教士因身体虚弱,辞去了澳门马礼逊中学校长的职务,准备偕夫人回国。他表示愿意带三五个旧徒,同赴新大陆,接受更完全的教育。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感到极其恐怖,但学徒中有一个名叫容闳的人,因想见大世面而自愿与其同赴美国。
容闳被布朗带到美国后,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咸丰五年(1855年)学成回国。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洗礼后,容闳“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认为要使中国达到文明富强的境界,只有让更多的人能接受到文明的教育。
同治七年(1868年),一直追随曾国藩创办洋务的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向曾国藩力荐容闳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设备,以创建日后著名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容闳得知丁日昌为朝廷命官,立即向他陈述中国应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同时,《中美续增条约》签订,其中第七条内容就是:“以后中国人若想进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按照对待最优国人民的办法一律照办。”它明确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法律依据。容闳提出派遣学生赴美就读的建议后,李鸿章马上表示大力支持,积极主张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他把选募学生出洋学习西学、培养人才视为中国自强的根本。
李鸿章接受丁日昌的推荐,委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和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办理幼童留学之事。陈、容拟定了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则,即出国留学章程,李鸿章认为为时过久、需费亦巨,建议先请试行,每年选送30名,以3年为期。恰好美国公使四月路过天津,李鸿章专门与之晤谈,就拟派幼童出洋学习一事,向该使咨询,对方的反应是“极为适当”。五月底,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李鸿章谈论起派幼童出洋学习之事,甚以为然。在与美、英公使先后会谈后,李鸿章对幼童留学一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六月二十六日,曾国藩、李鸿章联名致函总理衙门,正式阐明:拟选聪颖幼童送赴西方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都能精通,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八月十八日,曾、李又联衔上奏,请求恩准幼童出洋留学,派员在上海设局,访选沿海各省幼童,每年的名额为30名,4年计120名,分年搭船前往外国学习。不久,总理衙门复奏,同意了这一建议。
随后,“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设立,陈兰彬、容闳分别为正、副监督(委员),专门负责挑选学生出国。陈兰彬专司汉文和德行等事,容闳专司各学科事宜,财务则由他们共同主持。该局另设汉文教习二人,翻译一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单独上折奏请,令陈兰彬、容闳长期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清廷同时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事宜,决定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的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
陈兰彬、容闳与李鸿章磋商后,制定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共12条。他们指出:“西洋人游学他国,学有所长后,回国即请进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他们对于军政、船政,视之为身心性命之学。现在中国想要仿效西洋的做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应尽快遴选聪颖子弟,带到外国学习,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根据这个章程,容闳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因没有满额,容闳便到香港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补足数量”。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朝廷:“丁禹生屡来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计算、制造诸学,约计10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熟知,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曾、李皆为清廷举足轻重之能臣,因此他们的恳请很快得到了同治皇帝的恩准。清廷为此特别制定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容闳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副监督。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十一日,第一批30名中国幼童从上海出发,踏上了横渡重洋的航路。随后3年,清廷每年都派出数目相同的学生,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同治十三年(1875年)共派出4批120名留学生。挑选的少年年龄在11岁至16岁之间,每批一般有一名教习同行,教导他们中学课程,每个学生要在国外待15年,最后两年到各地游历。李鸿章要求驻美监督鼓励学生特别注意选修采矿和冶金专业。他还认为,适当延长留学期限,是培养中国学生,使他们回国后能胜任上海和北京新式学校的教师工作或在兵工厂、造船厂工作的最好方法。这些幼童大部分能够专心西学,品行端正,表现也堪称优良。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曾来函告诉李鸿章,说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
但是,派幼童出洋留学一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阻力是非常大的。李鸿章考虑到,容闳的海归身份不宜首当其冲,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或能服众,“利用陈兰彬的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微减少阻力”。这个破天荒的计划,在10年后还是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60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便返回中国,他们当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第三批学生由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人,在电线电报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业绩突出的,如黄仲良曾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实业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完成学业者中有50多人考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许多人卓有成就,其中包括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之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等。
詹天佑(1861年—1919年),汉族,字眷诚,号达朝,祖籍婺源,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现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甫西街芽菜巷42号),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被誉为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1905—1909年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创设“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在筹划修建沪嘉、洛潼、津芦、锦州、萍醴、新易、潮汕、粤汉等铁路中,成绩斐然;著有《铁路名词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
唐绍仪(1862年—1938年),字少川,1862年1月2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成员,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81年归国。唐绍仪曾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于1911年年底,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
唐国安(1858年—1913年),字国禄,号介臣,广东省香山县人(今珠海市唐家镇鸡山村)。他和唐绍仪既是同乡,是同学,又是同事,还是同宗同辈的叔伯兄弟,要想在内阁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不无可能,但他无意谋官,甘愿留在清华学校,独自主持校务,积极筹备复校,1912年4月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聘周诒春为教务长,晚年主持游美学务和清华工作,是容闳留美教育计划的“复活和延续”(台湾学者林子勋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日后清华学校发展成为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寿臣(1861年—1959年),原名周长龄,20世纪初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曾于1918年参与创立东亚银行,并担任该银行主席三十多年。作为政府及民间华人的沟通桥梁,他也是香港在殖民地时期第一名华人议政局成员。同时,周寿臣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曾经于1929年创立香港保护儿童会,又先后担任保良局及东华三院顾问一职。
由此可见,派幼童留洋一事,对于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又派遣淮军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7人,随同洋教习赴德意志学习陆军。第二年年初,李鸿章会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奏准,选派福建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同年,第一批赴欧学生出国。在法国学习制造的学生,多分赴各矿厂学习开采及冶炼、冶铸工艺诸法,均得到文凭,学成后还游历了英、法、比、德各国的新式机器船械各厂。赴英学习驾驶的学生,先入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后陆续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非洲、印度洋等处操练排布迎拒等方法;离船后又专请教习补授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均领有船长文凭。在这批留欧学生中,学习制造出色的有魏瀚、陈兆翱等,学习驾驶出色的有刘步蟾、林泰曾等。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鉴于学习制造的学生原定学制3年为期过于仓促,学习不够全面,建议改为6年;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仅有两个月在大的舰船上实习,阅历亦浅,所以他又建议每年改为6个月在船上实习,以增加阅历,但原定学制3年不改。
根据洋务事业的需要,李鸿章积极主张和大力支助中国留学事业,说明他与顽固守旧论者不同,能因时而变,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不像顽固守旧论者那样迂陋拘虚,冥顽愚昧,说出“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那样荒唐可笑的话,做出见人“掩面以避之”那样供西方人茶余饭后引以为笑柄的事来。这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吸收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复杂多变这个基本特征在李鸿章等有识之士身上的反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毫不退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李鸿章被解除职务后到德意志克虏伯炮厂访问。克虏伯热情地接待了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还专门为他出了一套纪念册。第二天,克虏伯亲自陪着李鸿章去看望中国留学生。李鸿章对留学生们说:“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微奥妙,只要苦心研究,操练、演放、修整诸事赶紧苦学,必得其中奥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我已经老了,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侮保国的重任皆落在诸位双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