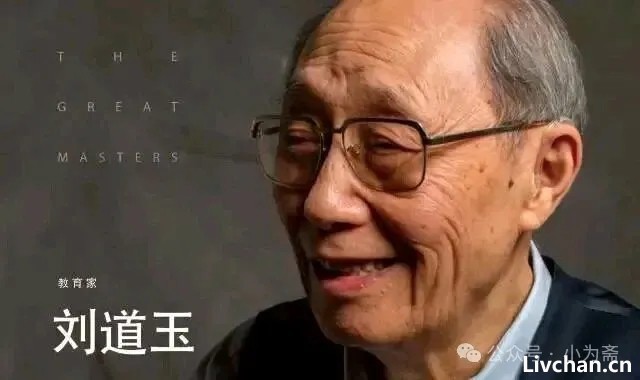科兴疫苗背后的资本故事,北大教授潘爱华的未名系帝国覆灭记
繁体曾几何时,疫苗接种点人头攒动,大家纷纷挽起衣袖,在医生准备打针时,得知了疫苗的名称——“科兴”。
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在2021年创造1280亿营收、956亿净利润的疫苗巨头,居然是一家外资控股公司,而它的创业起点竟与菜市场的豆芽摊紧密相连。

更令人唏嘘的是,科兴的崛起与陨落背后,交织着两位昔日合作伙伴——尹卫东与潘爱华长达二十年的爱恨情仇,以及一个北大教授打造的未名生物帝国如何在资本游戏中土崩瓦解的故事……
80年代末,上海甲肝疫情如黑色浪潮席卷,31万人感染的惨烈数据刺痛了26岁的尹卫东。在唐山市卫生防疫站工作的他,见过太多患者在痛苦中离世,这促使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辞职创业,研发甲肝疫苗。
尹卫东揣着5万元积蓄和一纸研发方案,在菜市场租下一间简陋小屋。白天,他像普通商贩一样蹲守摊位,潮湿的豆芽筐旁,烧杯、试管与电子秤挤在一起,构成了最奇特的“实验室”;夜幕降临,他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仔细记录着每一组实验数据。
这样白天卖豆芽、夜晚搞科研的日子,他咬牙坚持了整整十年。
几乎在同一时间,北京大学未名湖畔,34岁的潘爱华与31岁的陈章良这两位年轻学者,凭借学校提供的40万元启动资金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创办了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
然而,90年代的中国疫苗产业尚处萌芽阶段,潘爱华与尹卫东虽然都对疫苗研发有着一定天赋与执着,但想取得成功,仍需继续努力。
命运的齿轮在1998年转动,彼时,已在生物医药领域崭露头角的北大教授潘爱华受邀参加一场学术会议,遇上了尹卫东和他新研发的甲肝疫苗。

这位极具商业眼光的学者,当场拍板拿出5100万元,与尹卫东共同创立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潘爱华以资金入股占股76%,尹卫东以技术入股占24%。同年,科兴自主研发的甲肝灭活疫苗获批,成为国内首个国产甲肝疫苗。
潘爱华此时正值人生高光时刻。除北京科兴外,他掌控的未名系还包括深圳科兴和厦门未名(专注神经生长因子研发),形成了覆盖生物制药全产业链的布局。
一位未名老员工回忆:“潘教授当时经常说,未名要做中国的基因泰克(Genentech,全球首家生物技术公司),让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站上世界舞台。”
2003年非典疫情成为科兴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在抗疫过程中,尹卫东敏锐意识到资本市场对生物医药企业的重要性,开始筹划科兴赴美上市。
为满足纳斯达克上市要求,科兴生物的控股实体注册于安提瓜和巴布达,并通过复杂的离岸架构实现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潘爱华原本51%的控股权被大幅稀释至26.9%,而尹卫东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将实际控制权转移至海外注册的科兴控股名下。
可见,尹卫东团队更熟悉国际资本规则,潘爱华虽然学术造诣深厚,但对这些金融操作的理解慢了半拍。

2004年12月,科兴生物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中国首家在美国上市的疫苗企业。上市后的科兴生物间接控制四家内地运营子公司:北京科兴、大连科兴、科兴中维和科兴中益。
外资股东的悄然入场始于上市前后。赛富亚洲基金、鼎晖投资、永恩资本、维梧资本等机构投资者陆续进入,这些外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很快超过38%。
值得注意的是,赛富亚洲基金的前身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正是日本软银集团旗下投资机构,这解释了为何后来有报道称科兴“最大股东是日本软银”。
在一系列合作和并购上,尹卫东成为外资股东最信任的代言人,潘爱华却仍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
直到2015年,中概股回归潮兴起,科兴生物也启动私有化进程。正是这一决定,彻底激化了潘爱华与尹卫东之间积累十余年的矛盾,私有化方案的严重分歧使两位创始人彻底走向对立。
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等外资股东提出以6.18美元/股的价格将科兴生物私有化,而潘爱华则主张联合中信集团等国内资本,以7美元/股的更高价格竞购,目标是让科兴回归A股市场。
从两个人的想法来看,尹卫东坚持国际化资本路线,而潘爱华希望将科兴纳入“国产疫苗国家队”体系。
为达成目的,潘爱华使出一系列“非常手段”。比如,他通过未名医药控制的北京科兴拒绝向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数据,导致科兴生物无法按时提交年报而停牌;他实名向中央纪委举报尹卫东涉嫌行贿、职务侵占等罪名。
更戏剧性的是,他派人强行接管北京科兴的厂房,上演了一出“武装夺权”的闹剧。
这场混战导致科兴生物股票停牌长达四年之久(2019-2023),公司运营受到严重影响。外资股东们却在这场内斗中渔翁得利,进一步巩固了控制权。
截至2021年,科兴生物前五大股东中,赛富亚洲基金持股15.07%,鼎晖投资、永恩资本、维梧资本等合计持股超38%,而创始人尹卫东仅持股8.89%,潘爱华的未名系更是被边缘化。
可谁都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将科兴生物从内斗泥潭带上全球舞台中央。

2020年,尹卫东抓住机遇,启动“克冠行动”,在政府支持下迅速研制出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2021年6月,该疫苗被WHO列入紧急使用清单,截至2022年初,全球供应量突破27亿剂。
如此大的供应量,带来的是巨大的收入,2021年,科兴生物营收达128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94%;净利润9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08%。这意味着科兴日均盈利约3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些天文数字的背后,却是一个令国人五味杂陈的事实——近半数利润流向了外资股东口袋。
与此同时,潘爱华的未名系却错失了这场千亿盛宴。由于控制权争夺,未名医药虽持有北京科兴26.91%股权,却无法对新冠疫苗业务施加影响。因为尹卫东早已通过2009年成立的科兴中维(独立于北京科兴)作为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主体。未名医药仅在2021年获得4.7亿元投资收益,勉强弥补了主营业务亏损。
颇具戏剧性的是,当尹卫东借助新冠疫苗登上事业巅峰时,潘爱华的未名帝国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
2014—2019年间,潘爱华在全国三四线城市大举投资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近千亿元,包括合肥、保定、北戴河三个“千亿级产业园”。
随着2018年后房地产调控收紧,这些项目纷纷烂尾,未名集团资金链断裂,潘爱华开始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救急。2017—2019年间,未名集团累计非经营性占用未名医药资金达9.22亿元。这些违规行为引发监管层层关注,未名医药收到多封警示函。
控制权的彻底丧失发生在2022年。因债务违约,潘爱华持有的未名医药股份被法院分批拍卖。
真正将潘爱华送入监狱的是2022年的“厦门未名增资闹剧”。在明知失去未名医药控制权的情况下,潘爱华联合厦门未名董事长罗德顺及杭州强新法人李鹏飞,秘密签署协议,使了一招“空手套白狼”。
这场闹剧很快败露。2022年8月,投资者通过工商登记发现异常后举报,未名医药新管理层报案。202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法院判决:潘爱华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处罚金100万元;责令返还厦门未名34%股权及1275万元资金。与他一同获刑的还有罗德顺(7年)和李鹏飞(8年)。
尽管三人均提出上诉,但这位曾获国际大奖的北大教授,商业生涯已注定以悲剧收场。
2025年的今天,科兴生物与未名系的命运轨迹已截然不同。尹卫东领导的科兴正加速全球化布局,在70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2024年海外收入增长超60%,预计2025年海外销售将增长200%—400%。
这家疫苗巨头已转型为“全球化生物制药平台”。

而潘爱华的未名系已分崩离析。北大未名集团官网最后一次更新停留在2023年,其宣称的“生物经济体系”已成过眼云烟。
假如历史能重来,潘爱华当年保住自己的控股权,未名系可能就是今天的疫苗之王,也能做到日入3亿的神话。
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尹卫东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从草根创业者到商业领袖的蜕变。潘爱华却从万众敬仰的北大教授,成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
来源:百晓生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