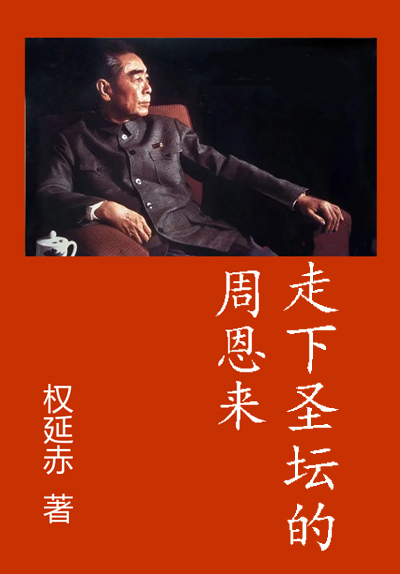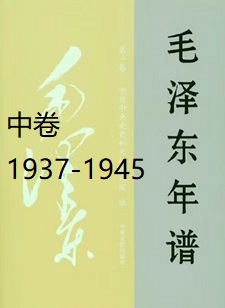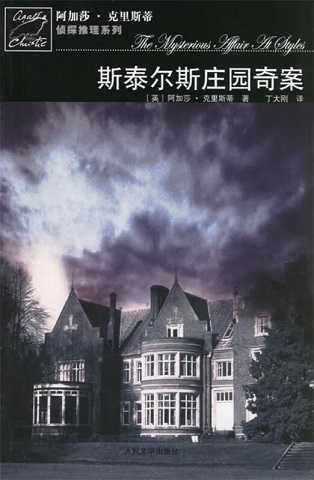【原文】
先生曰:“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翻译】
先生说:“学问也需要别人的点化,但总不像自己理解觉悟的那样一了百当,否则的话,即使别人点化再多,也没有作用。”
【原文】
“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
【翻译】
“孔子的气魄很大,凡是帝王的伟业,他无一不会领悟到,但也都只是从他自己的心上生发来的。就像大树,它有许多的枝叶,但也都只是从根本上培养功夫,所以能长成这样,而不是从枝叶上做的功夫。学者们向孔子学习,却不学着在心上用功,只是心急火燎地去学习他的大气魄,这是把功夫做反了嘛。”
【原文】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①,其流必归于文过。”
【注释】
①甑(zēng):古代炊具。
【翻译】
“人犯了过错,大多会在那个过错上用功。这就像是补破了的饭甑,必然会有文过饰非的弊病。”
【原文】
“今人于吃饭时,虽无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翻译】
“现在的人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其他事情摆在眼前,他们的心仍然忧虑不止,只因为自己的心忙碌惯了,所以收都收不住。”
【原文】
“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
【翻译】
“琴瑟与书籍,这两者学者们缺一不可,因为有了事情做,心就不得放纵了。”
【原文】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
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翻译】
先生感叹说:“世间懂得学问的人,就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不到‘善与人同’。”
崇一说:“这个毛病实际上只是个好高骛远,不能舍己从人罢了。”
【原文】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
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翻译】
问:“良知原本是中和的,却怎么会有过和不及的现象呢?”
先生说:“知道了过和不及的地方,就是中和了。”
【原文】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①
【注释】
①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语出《大学》。意为上级的无礼让我讨厌,将心比心,我对下级不要无礼。
【翻译】
先生说:“《大学》里说的‘所恶于上’,就是良知;‘毋以使下’,就是致知。”
【原文】
先生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①,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注释】
①肯綮(qìng):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要害处。
【翻译】
先生说:“苏秦、张仪的智谋,也是圣人的资质。后代的许多事业文章和豪杰名家,都只学到了张仪、苏秦的旧智慧。而苏秦、张仪的学术里,善于揣测人情,没有哪点不是说中了别人的要害,所以说他们的学问真是难以穷尽。张仪、苏秦也能看到良知的妙用处,只是没有把它们用在善上面。”
【原文】
或问“未发”“已发”。
先生曰:“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
问曰:“‘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譬如钟声,未扣不付谓无,即扣不付谓有。毕竟有个扣与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即扣时也只是寂天默地。”
【翻译】
有人请教“未发”和“已发”的问题。
先生说:“只因为后世儒生们已经把‘未发’和‘已发’分开来说了,所以,我只能说个没有未发、已发,让人们自己思考明白。因为如果我说有已发、未发,听的人就还是会沦落到后世儒生们的见解当中去。如果真的明白了根本没有什么未发、已发,再说有未发、已发,那也无妨。因为原本就是有未发和已发存在的。”
又问:“未发,未尝不平和;已发,也未尝不中正。好比敲钟的声音,没有敲击的时候不能说它就不存在,而敲击了之后也不能说就有了。毕竟还是有个敲和没敲的区别。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没有敲的时候原来也是惊天动地的,敲打了之后,也同样是寂静的天地。”
【原文】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①,是从流弊上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
先生曰:“然。”
【注释】
①荀子性恶之说:荀子主张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翻译】
有人问先生:“古人谈论人性时,各有不同的说法,应该把哪种当成定论呢?”
先生说:“人性没有固定的体,因此关于它的论述也没有定论。有从它的本体上谈论的,有从它的作用上说的,有从它的源头上谈论的,有从它的流弊上说的。总而言之,人性唯有一个,只是人们对它的见识有浅有深罢了。如果你执着在哪一个方面,就会出错。人性的本体,原来就是无善无恶的。而它的运用与流弊,也是有善有恶的。就好比眼睛,有喜悦时的眼睛;有发怒时的眼睛;直视的时候,就是在看的眼睛;偷看时,就是窥视的眼睛,等等。总而言之,还只是这一双眼睛。如果人们看见了发怒时的眼睛,就说从没有过喜悦的眼睛;看到直视时的眼睛,就说没有看到过偷窥的眼睛。这都是执着的表现,是错误的。孟子说人性,是直接从源头上来说的,也只不是说了个大概;荀子‘性恶’之说,则是从它的流弊上说的,也不能完全说他不对,只是不够精全罢了。但是普通人却失去了心的本体。”
问的人说道:“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求人们在源头要弄明白;而荀子则是从流弊上说性,功夫都用在末流上,以求费力补救。”
先生说:“是这样的。”
【原文】
先生曰:“用功到精处,愈著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著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
“杨慈湖①不为无见,又著在无声无臭上见了。”
【注释】
①杨慈湖:杨简(1140~1226),字敬仲,号慈湖,浙江慈溪人。陆九渊弟子,南宋哲学家,官至宝漠阁学士。
【翻译】
先生说:“功夫越到了精妙的地方,越不能用语言表达,说理就越困难。如果执意于在精妙的地方,全体的功夫反倒会被拘泥了。”
又说:“杨慈湖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他又执意于无声无臭上罢了。”
【原文】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岩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
【翻译】
“人在一天当中,就把古今的世界都经历了一遍,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当夜气清明的时候,没有视觉和听觉,也没有思虑与行动,心怀平定淡然,这就是羲皇的世界;而清晨的时候,神清气朗,气息明朗,庄严肃穆,就是尧、舜时代的样子;到了中午之前,人们用礼仪交往,气度井然,就是夏、商、周三代时的状况;而到了正午之后,神气渐昏,人事往来繁乱,那就是春秋战国时的世界。待到渐渐进入了昏夜,万物都安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灭的世界了。学者只要信得过良知,不被气扰乱,就能时时都做个羲皇时代的人。”
【原文】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
诸友请问。
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方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翻译】
薛侃、邹守益、马子莘、王汝止在先生身边侍坐,众人慨叹先生自征伐平定藩王以后,天下的诋毁和非议也与日俱增,于是先生让他们各自谈一下当中的缘故。有的说,先生的功业权势日益显赫,因此天下人有所嫉妒的一天天变多了;也有的说先生的学说日益昌明于天下,所以替宋儒争是非对错的人也就日益变多了;有的说自打正德九年(1514)以后,志同道合的人当中相信先生学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四方来的排阻的人也更加卖力了。
先生说:“你们各位所说的原因,当然也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方面,大家还没有提到。”
各位都向先生询问。
先生说:“我在来南京以前,尚有一些当老好人的想法。但是现在,我确切地明白了良知的是非,只管去行动,再不用有什么隐藏。现在我才真正终于有了敢作敢为的胸襟。即便天下人全都说我言行不符,那也毫无关系了。”
薛侃站出来说:“有这样的信念,才是圣人真正的血脉!”
【原文】
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
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涂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见之?”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惧。
【翻译】
先生点化学生的时候,往往一句话,便能感人至深。
有一天,王汝止出游回来。先生问他说:“你在外面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王汝止回答道:“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先生说:“你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话,满街的人反过来看你也是圣人。”
又有一天,董萝石也出游回来。他见到先生便说:“我今天看到一件奇怪的事。”先生说:“什么奇怪的事?”他回答说:“我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说:“这也只是寻常事情而已,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大概王汝止的棱角还没有磨去,而董萝石却早有省悟。所以虽然他们的问题相同,先生的回答却是不同的,先生是依照他们的话来启发他们。
钱德洪、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丙戌年(1526)的时候参加会试回来的路上,谈到先生的学说,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先生说:“你们扛着一个圣人去给别人讲学,别人看到圣人来了,早就吓跑了,这还怎么讲?必须做个愚夫愚妇,才能够去给别人讲学。”
钱德洪又说,现在要看出人品的高低是很容易的。先生说:“何以见得?”
钱洪答道:“先生您就像是泰山,摆在眼前,只有那些有眼无珠的人才会不知道敬仰。”
先生说:“但是泰山又比不上平地广阔,平地怎么发现呢?”先生这一句话,说破了我们终年好高骛远的毛病,在座的人无不有所警惧。
【原文】
癸未春,邹谦之来越问学,居数日,先生送别于浮峰。是夕与希渊诸友移舟宿延寿寺,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曰:“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一友问曰:“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
【翻译】
明嘉靖二年(1523)春天,邹谦之到浙江来求学。住了几天,先生到浮峰为他送行。晚上的时候,先生与希渊等几位朋友,留宿在延寿寺,众人秉烛夜坐,先生感叹惆怅不已,说:“江水滔滔,烟柳蒙蒙,谦之瞬间就到了百里之外的地方了。”
一位朋友便问:“为什么先生对谦之的思念这么深切呢?”先生说:“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样的人,和谦之非常接近啊!”
【原文】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
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翻译】
明嘉靖六年(1527)九月,先生重新被起用,再次奉命讨伐思恩(今广西武鸣县北)和田州(今广西田阳县北)。出征前,钱德洪和王汝中讨论先生的学问。汝中便引用先生的教诲说:“无善无恶才是心之体,而有善有恶则是意的作用,知道善恶是良知,而为善去恶则叫格物。”
德洪说:“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
汝中说:“这句话恐怕还只是个引子,没有说全。如果说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知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物。如果说意有善恶之分,那还是因为心体终究是有善恶之分存在的。”
德洪说:“心的本体是天生的性,本来就是无分善恶的。但是,人有受习性沾染的心,所以意念就有了善和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正是恢复心体的功夫。若果意本来就没有善恶,那么,谈功夫还有什么用呢?”
当晚,德洪和汝中在天泉桥坐在先生旁边侍坐,各人说了自己的看法,请先生来评判一下。
先生说:“现在我将要走了,正要给你们来讲明白这一点。你们两位的见解,恰好能够相互补充利用,不能够偏执于一方。我这里引导人,原本就只有两种:资质高的人,便直接让他们从本源上去体悟,而人的本体原本就是晶莹无滞的,原本就是未发之中的。所以资质高的人,只要稍稍去体悟本心就是功夫了。人和己、内与外一齐都悟透了。而资质较差的另一种人,他们的心难免受到了沾染,本体便被蒙蔽了,因此便暂且教他们在意念上去踏实地用功。等行善去恶的功夫纯熟之后,渣滓清除干净之后,人的本体也就自然明亮清洁了。汝中的见解,是我用来开导聪慧的人的说法;而德洪的见解,则是用来教导资质较差的人的说法。如果你们两位能够互相补充借用,那么,资质中等的人就都能够被引入正途了。而如果你们两位都偏执一个方面,那么眼下就会误导别人,对圣道也不能够穷尽。”
先生接着说:“以后与朋友们一起讲学,万万不能抛弃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要根据我这句话,因人而教,自然会没有问题的,这本来就是贯通上下的工夫。资质高的人,世上很难遇到了。能将本体功夫全都参透,这是连颜回、程颢也不敢自认的,又怎么敢随便对别人寄予这样的期望?人心受到了习性的沾染,如果不教导他在良知上切实地去下为善去恶的功夫,只去凭空想一个本体,对所有的事都不去切实地应对,只会养成虚空静寂的毛病。这个毛病可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不能不早跟你们说清楚。”
这一天,钱德洪和王汝中又有所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