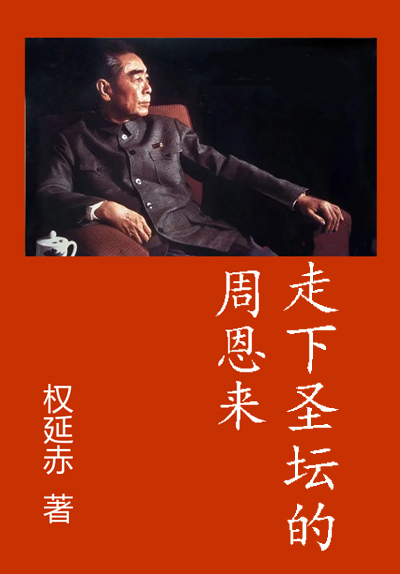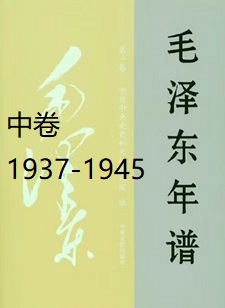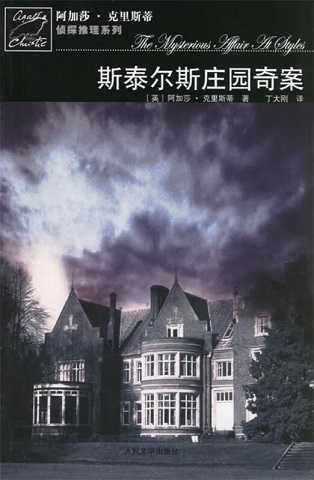【原文】
又曰:“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翻译】
先生又说:“眼睛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颜色作为本体;耳朵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声音作为本体;鼻子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气味作为本体;嘴巴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味道作为本体;心也没有本体,它以天地万物感应到的是非作为本体。”
【原文】
问“夭寿不贰”。
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翻译】
有人向先生请教“夭寿不贰”。
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对于一切声色、利益、嗜好,都能摆脱干净。但是只要还有一丝一毫在意生死的念头牵累着,便会有和本体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人有在意生死的念头,是生命本身带来的,所以不容易去掉。如果在这里都能看破、想透彻,心的全部本体才能自由没有阻碍,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原文】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
是友愧谢。
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
在坐者皆悚然。
【翻译】
一个朋友问先生:“想在静坐的时候,把好名、好色、好财的病根一一搜寻出来,清除干净,只怕也是剜肉补疮吧?”
先生严肃地说:“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的可以清除病根的,还是有大作用的。即使过了十几年了,也还能产生效用。如果你不用,就暂且把它存起来,别随便糟蹋了我的方子。”
于是朋友满怀愧疚地道了歉。
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想来也不能怪你,一定是我的门人里那些略微懂一些意思的人告诉你的,反倒耽误了你的理解。”
于是,在座的人都觉得汗颜。
【原文】
一友问功夫不切。
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①提起。一日,其徒将其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又何可提得?”
少间,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
先生旁顾曰:“我尘尾安在?”
一时在坐者皆跃然。
【注释】
①尘尾:拂尘。古人用动物的尾毛或麻等制作拂尘。
【翻译】
一个朋友向先生请教功夫不真切该怎么办。
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我已经用一句话包括尽了。现在怎么越说越远,全都不着根基了呢?”
朋友说:“您的致良知的学说,我们大概都已经听明白了,然而也还需要您再讲明一些。”
先生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致良知,又还有什么可以再说明的呢?良知本来就是清楚明白的,只需切实用功就行了。如果不愿切实地用功,只会在语言上越说越糊涂。”
朋友说:“正是要麻烦您把致良知的功夫说明白。”
先生说:“这也需要你自己去探寻,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告诉你。从前有一个禅师,当别人前来问法,他只会把尘尾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学生把他的尘尾藏了,想试试他没有尘尾怎么办。禅师找不到尘尾了,便只空着手把手抬起来。我的这个良知,就是用来解释问题的尘尾,没有这个,我有什么能提起来的呢?”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朋友来请教功夫的要点。
先生四顾旁边的学生们说:“我的尘尾在哪儿?”
于是,在座的人都哄然而笑。
【原文】
或问“至诚前知”①。
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邵子②必于前知,终是利害心未尽处。”
【注释】
①至诚前知:语出《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②邵子: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北宋哲学家,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屡授官不赴,后居洛阳,与司马光从游甚密,著有《皇极经世》等。
【翻译】
有人就《中庸》里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一句请教先生。
先生说:“诚,就是实理,也只是良知。实理的奇妙作用就是神;而实理萌发的地方,就是‘几’;具备了诚、神、几,就可以称为圣人。圣人并不重视预知未来。当祸福来临时,虽然他们是圣人,也难以避免。圣人只是明白‘几’,遇事能够变通罢了。良知没有前后之分,只要明白现在的‘几’,就能以一当百了。如果一定说要有‘前知’的心,那就成了私心,有趋利避害的意思。邵雍先生执着于‘前知’,恐怕还是他趋利避害的私心没有尽除的原因。”
【原文】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翻译】
先生说:“什么都知道但又什么都知道,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好像是太阳,它未曾有意去照耀万物,但又很自然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被太阳照射到的。无照无不照,就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什么都不知道,如今却要让它有知;本来良知是无所不知的,但现在却又怀疑它会有所不知。只是因为还不够信任良知罢了。”
【原文】
先生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翻译】
先生说:“《中庸》里说‘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以前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玄妙,如今再看才知道聪明睿智,原本就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耳朵原本就聪敏,眼睛原本就明亮,心思原来就睿智。圣人只是能做到一件事而已,那件能做到的事就是致良知。一般人做不到,也只是这个致良知。多么简单明了啊!”
【原文】
问:“孔子所谓‘远虑’①,周公‘夜以继日’②,与将迎不同,何如?”
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注释】
①远虑: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②夜以继日:语出《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翻译】
有人问先生孔子所说的“远虑”和周公说的“夜以继日”与刻意逢迎有何不同之处。
先生说:“‘远虑’并非指的是茫茫然地去思虑,只是要存养天理。天理在人们的心里,贯穿古今,无始无终。天理就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为了致良知。良知越想就越精明,如果不精深地思考,而只是随意地去应付,良知便会变得粗浅。如果以为远虑就是在事情上不着边际地思考,就难免会有毁誉、得失、人欲等掺杂其中,就成了着意逢迎了。周公夜以继日地思考,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明白了这一点,境界就自然与刻意地逢迎有区别了。”
【原文】
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①,朱子作效验说②,如何?”
先生曰:“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③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④,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无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注释】
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语出《论语·颜渊》。
②“朱子”句:朱熹《论语集注·颜渊》“极言其效之甚远而至大也”。
③八荒皆在我闼:宋人吕大临语,见《宋元学案》卷三十一。闼(tà),门楼上的小屋。
④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语出《论语·颜渊》。
【翻译】
有人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句,朱熹先生认为它是从效验上说的。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圣贤只是一个克己的学问。重视自己所下的功夫而不会这么重视效验。仁者与万物同为一体。如果不能做到与万物同体,只因为自己的私欲没有完全忘记。获得了全部的仁的本体,天下便全都归入到我的仁里面了,也就是‘八荒皆在我闼’的意思。天下能做到仁,那自己的仁也就在其中了。‘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仅仅是自己没有怨恨,就像‘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家庭、国家都没有怨恨,自己当然也就在其中了。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该重视的地方。”
【原文】
问:“孟子‘巧力圣智’①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②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③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注释】
①巧力圣智:语出《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全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不力也;其中,非不力也。’”②“三子”句:语出朱熹《孟子集注·万章下》:“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三子,指伯夷、伊尹、柳下惠。
③柳下惠:即展禽,名获,字禽,春秋时鲁国大夫,食邑在柳下,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
【翻译】
有人问:“孟子主张‘巧力圣智’的说法,朱熹先生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这样说对吗?”
先生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不仅有力,而且也还有巧,巧与力实际上并非两回事。巧也只在用力的地方,有力却不巧,也只不过是徒然,白费力气。用射箭做比喻的话,他们三个人里,一个能够步行射箭,一个能够骑马射箭,一个能够远程射箭。只要他们都能射到靶子那里,便都能叫作有力;只要能正中靶心,便都能叫作巧。但是,步行射箭的不能够骑马射箭,骑马射箭的又不能远程射箭,他们三个各有所长,才力各有不同的地方。而孔子则是身兼三长,然而,孔子的‘和’最多也只能达到柳下惠的水平,而‘清’最多能够达到伯夷的水平,‘任’也最多只能达到伊尹的水平,未曾再添加什么了。如果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他们的力加在一起反倒能超过孔子了。巧、力只是为了阐明圣、智的含义。如果认识到了圣、智的本体,自然就能够明了了。”
【原文】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违’①,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②,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霆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是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
【注释】
①“先天”句:语出《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②“后天”句:同上。
【翻译】
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就是天。”
“良知仅是辨别是非的心,而是非仅是个好恶。明白了好恶,也就是穷尽了是非;而明白了是非,也就穷尽了万事万物的变化。”
又说:“‘是非’两个字是大规矩,而灵巧的地方就在乎于个人了。”
“圣人的良知,就像青天里的白日;而贤人的良知就像有浮云的天空里的太阳;愚人的良知则像阴霾天气里的太阳。虽然他们的明亮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一样能够分辨黑白的,即使在昏暗的夜里,也能够影影绰绰地辨别出黑白来,因为太阳的余光仍旧没有完全消失。在困境中学习的功夫,也只是从这一点光明的地方去精细鉴察罢了。”
【原文】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
【翻译】
有人问先生:“良知就像太阳,而人的私欲就像是浮云。浮云虽然能够遮蔽太阳,然而也是气候里本就具有的。莫非人的私欲也是人心本就具有的吗?”
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就是所谓的‘七情’。这七种感情都是人心本来就具有的,但我们需要把良知体认清楚。就比如太阳光,也不能指定一个方向照射。只要有一丝空隙,都会是太阳光的所在之处,即使布满了乌云,只要天地间还能依稀辨别形色,也是阳光不会磨灭的表现。不能因为浮云遮蔽了太阳,就强求天空不再产生浮云。上面所说的七种情感顺其自然地运行,都是良知在发生作用,不能认为它们有善、恶的区别,更不能对它们太执着。如果执着于这七情,就成了‘欲’,都是良知的阻碍。然而刚开始执着的时候,良知自然能够发觉出来,发觉后便会马上清除这一阻碍,恢复它的本体。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看透,才是简易透彻的功夫。”
【原文】
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的,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翻译】
有人问:“圣人生知安行是天生就有的,这话对吗?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功夫呢?”
先生说:“‘知’‘行’二字,就是功夫,只是这功夫有深浅难易的区别罢了。良知本来就是精明的,比如说孝敬父母,那些生知安行的人,只不过是依照自己的良知,切切实实地去尽孝而已;而那些学知利行的人,则需要时时反省察觉,努力地去依照良知去尽孝而已;至于那些困知勉行的人,他们受到的蒙蔽禁锢已经非常深,虽然需要依照良知去尽孝,但是又被私欲阻碍,因此不能够做到尽孝。这就需要他们用别人一百倍、一千倍的功夫,才能够做到依照良知去尽孝。圣人虽然是生知安行的,但他们在内心里也不敢肯定自己,所以愿意去做困知勉行的功夫。那些困知勉行的人,却时刻想着去做生知安行的事,这怎么可能成功呢?”
【原文】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①,周公系爻②,孔子赞《易》③,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注释】
①彖(tuàn):《易传》中说明各卦基本观念的篇名。分《上彖》《下彖》两篇。
②爻(yáo):指爻辞。说明《周易》六十四卦中各爻要义的文辞。每卦六爻,每爻有爻题和爻辞。爻题都是两个字:一个字表示爻的性质,阳爻用“九”,阴爻用“六”;另一个字表示爻的次序,自下而上,为初、二、三、四、五上。如乾卦初爻:“初九,潜龙勿用。”“初九”是爻题,“潜龙勿用”是爻辞。
③《易》:指《易传》。是对《易经》所做的各种解释。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亦称《十翼》。相传为孔子作。据近人研究,大抵系战国或秦汉之际的作品。
【翻译】
有人问先生道:“快乐才是心的本体,但是遭遇到了大的变故的时候,痛心哭泣,不知道这时本体的快乐是不是还存在?”
先生说:“必须是痛哭一番之后才会感觉快乐,如果没有哭,也就不会觉得快乐了。虽然是在哭,自己的内心却得到了安慰,这也是快乐啊。快乐的本体未曾有什么变化的。”
又问:“良知唯有一个而已。但是文王作象辞,周公作爻辞,孔子写《十翼》,为何他们看到的理都分别有所不同呢?”
先生说:“圣人岂会拘泥于死旧的模式呢?只要都同样是出自于良知,即便他们各自立说又何妨呢?就以一园翠竹打比,只要枝节相差不大,就是大同。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每一根的枝节都一模一样,那就并非是自然的神妙造化了。你们这些人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相同,就不妨各自间有些差异存在了。你们这些人如果不愿意用功,就连竹笋都还没有生长出来,到哪里去谈论枝节呢?”
【原文】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
柴鸣治入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
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间大慈的父。”
鸣治愕然请问。
先生日:“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个慈父。”
【翻译】
乡下有两父子要打官司,请先生裁决。侍从们想要阻止他们,先生听说了之后,开导的话还没有说完呢,父子两个就已经就抱头恸哭,然后相拥着离开了。
柴鸣治便进来问道:“先生的什么话让他们这么快速地感动悔悟了?”
先生说:“我跟他们说舜是世界上大不孝的儿子,而瞽瞍则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鸣治惊讶地问先生为什么。
先生说:“舜常常觉得自己大不孝,所以他才能尽孝;而瞽瞍常常自以为自己是很慈爱,所以他不能做到慈爱。瞽瞍只记得舜是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就不曾取悦过自己呢?他不明白自己的心已经被后妻改变了,仍然觉得自己是慈爱的,因此就越发不能做到对舜慈爱。而舜则只想着从小开始,父亲照顾自己的时候是如何如何地疼爱自己,可是现在却不疼爱了,恐怕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孝,所以每天都在想自己没有做到尽孝的地方,所以他就越发能尽孝了。等到瞽瞍高兴的时候,也不过是恢复了心里慈爱的本体。所以,后人都把舜当成是古今的大孝子,而认为瞽瞍则是个慈爱的父亲。”
【原文】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①。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注释】
①“孔子”之句: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翻译】
先生说:“有农夫前来找先生请教,孔子也不会事先准备好了知识来回答他。孔子的内心也是空无一物的。但是他可以帮助农夫分析他心里明白的是非,替他做出一个决策,这样农夫的心便比较开朗了。农夫知道自己的是非,便是他原本就有的天然准则。虽然圣人聪明,但对这种准则也无法有丝毫的增减。只是他们不够自信,所以孔子给他们进行了剖析之后,他们心里的是非曲直就会显现无余了。如果孔子和他们说话时,还保留有一些知识在他们心里,就不能够尽显他们的良知了,而道体也就分为两处了。”
【原文】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奸’①,本注说象已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②。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注释】
①烝烝乂,不格奸:语出《尚书·尧典》“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瞽子,指舜。象,舜之弟。烝,进。乂(yì),治理,安定。格,至。
②“本注”二句:汉代孔安国传注说:“谐,和。悉,进也。言能以至孝和谐顽象昏傲,使进进以善白治,不至于奸恶。”
【翻译】
先生说:“《尚书》中的‘烝烝乂,不格奸’,孔安国的本注认为,象已经慢慢上进到了道义的境界,而不至于去做大奸大恶的事。舜被尧征召之后,象仍然整天想要把舜杀死,这是何等奸邪的事?而舜则只是学习自己修养、自我克治,不直接去纠正他的奸恶,而是用自己的克制来感化他。文过饰非,用以掩盖自己的奸恶,这是恶人们的常态;如果去指责他的是非,反倒会激发他的恶性。舜最初让象起念杀害自己,也是因为想让象变好的心意太过急切,这就是舜的过错。等事情过了之后,才明白原来功夫只在自己,不能责备别人,因此最后能有‘克谐’的结局。这就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地方。古人的言论,都是自己经历过的,所以说得特别确切。而流传到了后代,歪曲变通,仍然合乎人情。如果不是自己曾经经历过,又怎能体会到古人的苦心呢?”
【原文】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①,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曰:“洪要求元声②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
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
对曰:“古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
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
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必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
【注释】
①九成:九乐章。下文“九变”即九成。“韶”为舜的乐,“武”为武王的乐。
②元声:古代律制,以黄钟管发出的音为十二律所依据的基准音。故称元声。
【翻译】
先生说:“古乐不流行已经很久了。现在戏曲倒有些与古乐能意思相近。”
德洪不懂,便向先生请教。先生说:“《韶》乐里的九章,都是舜的一个戏本;而《武》乐的九变,是武王的一个戏本。圣人一辈子的事迹,都被记录在戏曲当中了。所以,德行高尚的人听了,就明白他是尽善尽美的还是尽美而未尽善的。后代人写作乐曲,只作一些陈词滥调,跟教化民风全然没有关系,这怎么能用来感化百姓呢,怎么能让风俗淳善呢?现在要让民俗返璞归真,把当今的剧本里的妖淫词调都去删除掉,只利用起当中忠臣孝子的故事,让愚昧无知的百姓们都懂得其中的道理。在不知不觉中感化他们的良知,这样对风化才会有好处。同时,古乐也就逐渐恢复本来面貌了。”
德洪又说:“我连找基准音都找不到,只怕古代的音乐也很难得以复兴吧。”
先生问:“你觉得基准音应该到哪里去寻找?”
德洪回答说:“古人制测管来测量气候的变化,这应该是寻找元声的办法。”
先生说:“假若要从葭灰黍粒中寻找元声,好比就是水底捞月,这怎么能成功呢?元声只能去内心寻找。”
德洪问:“在心上如何寻找呢?”
先生说:“古人大治天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心平气和,然后才是作礼乐教化。就像你吟诵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何苦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德洪又问问:“那么,古人用律管测量气候的方法,根据又在哪里呢?”
先生说:“古人具备了中和的本体之后,才去作乐。而心体的中和,原本就是与天地间的气相相符合的。候天地之气,与凤凰的鸣叫相谐,不过是为了验证我的气是不是真的中和,这是制定了音律之后的事情了,不一定要依据这个才能制定音律。如今通过律管来候气,必须确定在冬至这天,但是,当到了冬至子时,只恐又不准确,又到哪里去找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