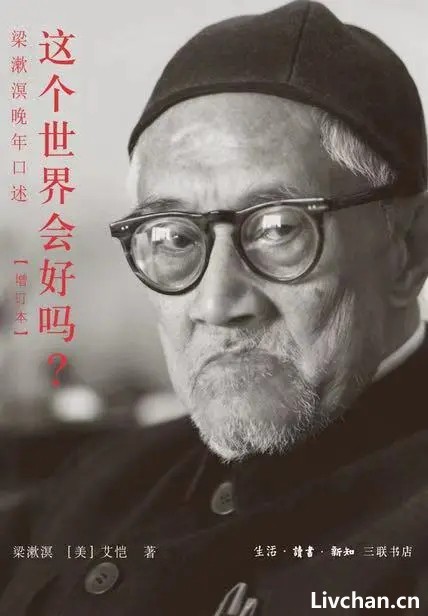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吗?——一个真实的事件
繁体在自然状态下,自保和惩罚罪犯,是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为了活命,生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就像《芙蓉镇》的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但是,人,为了生存,真的可以不择手段吗?在极端状态上,是否可以将别人作为工具?
生存第一,还是道义原则第一?
这便是一百多年前英国“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提出的问题。
这个案子,也叫木犀草号案,或者又叫帕克案。木犀草号是一艘船,杜德利和斯蒂芬是船长和大副,帕克全名是理查德·帕克,是案件中的受害者。
“英国女王诉达德利和斯蒂芬斯案”(R v Dudley and Stephens)是法理学和伦理学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深刻地揭示了实在法与自然法、功利主义与绝对道德律令之间的张力。
一、 案件事实背景:海上生存的残酷抉择
1. 时间与地点:1884年,南大洋,距离好望角约1600海里。
2. 人物:
托马斯·达德利(Thomas Dudley):船长
埃德温·斯蒂芬斯(Edwin Stephens):大副
埃德蒙·布鲁克斯(Edmund Brooks):船员
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17岁的船舱服务员,孤儿
3. 事件经过:
“木犀草号”出海后,遭遇暴风雨,船只沉迷,四人逃上救生艇。
他们仅有少量罐头萝卜,没有淡水。在海上漂流20天后,他们以海龟和尿液维生。
帕克因不听劝告喝了海水,病倒并变得虚弱不堪。
在第19天,达德利提议:为了其余人能活下去,应该抽签决定杀死并吃掉其中一人。布鲁克斯反对。
第20天,达德利和斯蒂芬斯在布鲁克斯未明确表态(但未再反对)的情况下,由达德利动手杀死了已昏迷的帕克。
三人以帕克的尸体和血液为食。四天后,他们被路过的德国船只“福佑号”救起。
二、 法律审判与核心争议
回到英国法尔茅斯港后,达德利和斯蒂芬斯被逮捕并以谋杀罪起诉。
辩方论点(核心是“必要性”辩护):
1. 生存必需:在极端生存环境下,杀死一人是让其他人活下来的唯一手段。
2. 功利主义计算:牺牲一人(且是当时最虚弱、可能最先死去的)的生命,拯救三人,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3. 帕克的“可牺牲性”:帕克是孤儿,无牵无挂;且他已病重,生存希望最渺茫。达德利甚至声称,是帕克本人先提出了抽签的建议(但无证据)。
4. 惯例:辩方援引了海上惯例,认为在极端情况下,此种行为被认为是“紧急避险”,是被默许的。
检方及法庭观点:
1. 谋杀罪的绝对性:英国法律中,谋杀是重罪,没有任何成文法或先例允许以“必要性”为由故意杀害一个无辜的人。
2. 生命的不可比较性:任何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法律不能也无法衡量一个年轻体弱者的生命与三个年长强壮者的生命孰轻孰重。
3. 知情同意的缺失:法庭特别指出,如果达成了某种公平的协议(如抽签),所有参与者都自愿承担风险,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本案中,帕克完全没有机会同意或参与决策,他纯粹是被动的牺牲品。
4. 社会后果:如果允许这种“必要性”辩护,很有可能将打开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导致强者可以任意牺牲弱者,法律秩序将崩溃。
三、 判决与后续
判决:法庭最终裁定达德利和斯蒂芬斯谋杀罪成立,判处他们死刑。判决书这样写道:“一个人为了不被饿死,杀吃了另一个人,虽然当时的处境下,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保存生命的唯一机会,但他还是犯了谋杀罪。”
由于舆论普遍同情被告,以及案件的特殊性,两名罪犯获得获得了“赦免”,并且其死刑判决被减为了6个月监禁。
四、 政治哲学角度的剖析
这个案件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它直指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人间的法律与自然法则发生冲突、最基本的生存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何种价值优先?
1. 功利主义 vs. 道义论
功利主义(如边沁、密尔):此案仿佛是为功利主义量身定做的考题。从后果看,杀一人救三人,净收益是两条生命,似乎是最优解。达德利和斯蒂芬斯的逻辑是典型的“行为功利主义”。
道义论(如康德):康德会严厉批判这种行为。根据绝对命令,人永远不能仅仅被当作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而应始终被视为目的本身。杀死帕克,纯粹是利用他来延续其他人的生命,严重侵犯了他的尊严和自主性。对于康德而言,道德律令是绝对的,不容因结果而妥协。
2. 自然法 vs. 法律实证主义
自然法(如阿奎那、洛克):自然法理论认为,存在一种高于人定法的、源于自然和理性的道德法则。其中,自我保全是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辩方可以主张,在“自然状态”下,生存是最高法则,他们的行为符合自然法。
法律实证主义(如奥斯丁):实证主义强调“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在本案中,英国成文法明确规定了谋杀罪,且没有“生存必要性”的例外条款。因此,法官必须依法判决,无论其道德后果如何。此案的判决,恰恰捍卫了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避免了司法滑向个案化的道德评判。
3. 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
我们可以将救生艇视为一个微型的“自然状态”。当社会契约和公民政府失效时,人们会退回何种境地?
霍布斯会认为,在没有公共权力的状态下,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每个人对一切事物都有权利(甚至是彼此的生命),这将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达德利的行为仿佛是霍布斯式自然人的体现。
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中依然要遵守自然法,即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无故杀死帕克,即使是为了生存,也违反了自然法。
案件的判决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契约的重申:一旦回到文明社会,就必须重新接受法律和道德的绝对约束。个人不能将自然状态下的生存逻辑带入公民社会。
五、案件判决与赦免:法律与人性的妥协
这个案件的判决非常有意思。法院以谋杀罪判决两人死刑,但女王的政府对其二人赦免,减刑6个月,其实当时已经羁押好长时间,实质就是宣判后就释放。这个结果,反映了国家在面对极端伦理困境时的复杂考量:
A. 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坚持原则)
法庭必须做出有罪判决。这是为了确立一个不容置疑的先例:
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随意剥夺,法律面前没有“吃人”的特权。
如果法庭判决他们无罪,就等于承认在极端情况下,个人可以成为他人的生存工具,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法律保护每个人平等生命权的基石。
B. 承认人性的脆弱与处境的特殊性(体现人性)
同时,法官和行政当局也清楚地认识到,让这两个在极端生存压力下做出选择的人走上绞刑架,是极其残酷和不近人情的。公众的广泛同情也反映了普遍的道德直觉:在那种绝境下,大多数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会做出更“道德”的选择。
C. 精妙的“分工协作”: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法院扮演了 “原则的守护者”:它坚守了法律的底线,确保了规则的清晰和权威。它的判决向社会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样做在法律上是有罪的。”行政系统(内政部和女王) 扮演了 “仁慈的施行者”:它通过赦免权,缓和了法律严格适用所带来的严苛后果,体现了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灵活性。
D. 规则偶尔有例外。在人类事务中,规则与人情发生碰撞,如何取舍?如何应对规则的例外情况?如果法律直接承认“例外”(即判决无罪),那么“生命不可侵犯”这一根本规则就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导致未来类似情况下的滥用和司法混乱。如果法律完全无视“例外”(即执行死刑),则会显得僵化、冷酷,背离了民众的正义感。于是,该案找到了一条极具智慧的中间道路:“我们通过定罪来维护规则的神圣性;我们通过赦免来承认处境的特殊性。”这等于在说:“法律上,你们是错的,必须被定罪;但人性上,你们的情有可原,值得被宽恕。”
E.进一步讨论:在个体的生命和权利保护上,国家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国家(以法院为代表)是否有权对身处绝境、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行为进行审判?其正当性何在?
总而言之,“女王诉达德利案”不仅仅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法律案件,更像是一个政治哲学的寓言,让我们思考个人与共同体、生存与道德、法律与良知之间永恒的张力。
来源:哲学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