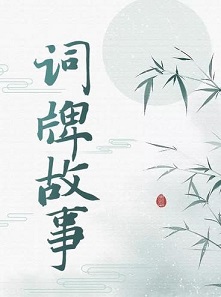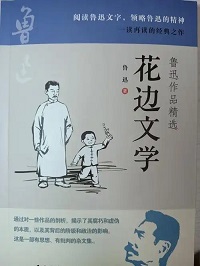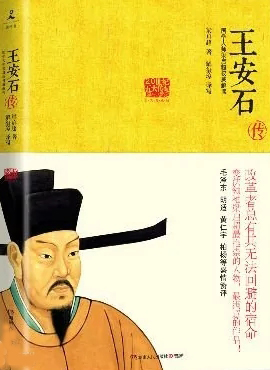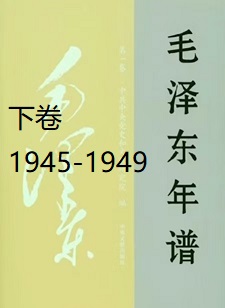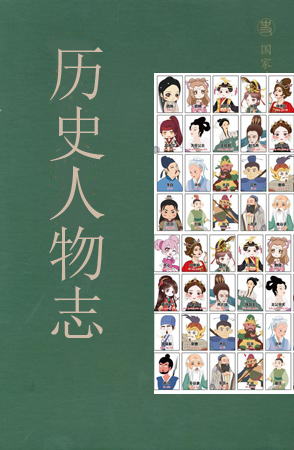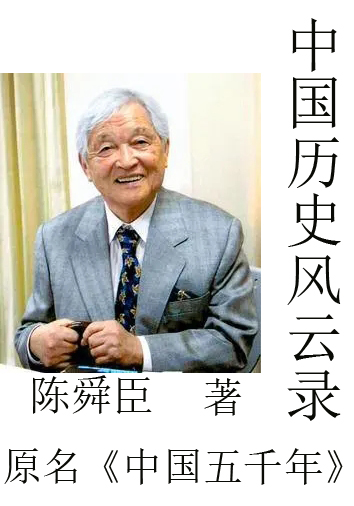第一章 血案惊魂:测谎仪锁定的 “凶手”
2002 年 5 月 31 日清晨,河南浚县黎阳镇东马村的薄雾尚未散尽,一阵凄厉的哭喊划破村庄的宁静。村民陈连荣家中,女主人倒在卧室血泊中,7 岁的儿子马昂、4 岁的女儿马萌蜷缩在床边,一家三口全部遇害。法医鉴定显示,陈连荣母子系锐器切断颈动脉失血身亡,幼女则被单刃刺器刺入颈椎致命,现场留下的血袜印与血拖鞋印,成为唯一的 “线索”。
此案惊动公安部,浚县公安局局长立下 “三月必破” 的军令状,百余名警力进驻村庄,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接受了讯问。38 岁的马廷新此时还在村外的养鸡场忙碌,作为畜牧局下岗职工,他靠养鸡维持生计,妻子菅素玲在村小代课,日子平淡安稳。两家虽因父辈矛盾和两年前的争执有嫌隙,但马廷新从没想过,自己会与这起灭门案扯上关系 —— 他甚至还在给专案组驻扎的饭店送鸡蛋。
转折出现在 8 月底的一次测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专家带着设备进驻浚县宾馆,马廷新与几名村民一同接受测试。简单问询后,测谎人员突然指着他:“就是他,人就是他杀的。” 这份缺乏科学定论的测谎结果,成了锁定嫌疑人的关键。更 “巧合” 的是,5 位足迹鉴定专家联合出具报告,称现场血袜印 “系马廷新右脚所留”,尽管辩护律师后来发现,现场只有左脚印,且步幅与马廷新的行走特征明显不符。
2002 年 12 月 14 日,马廷新被刑事拘留。被带走时,他反复强调:“案发当晚我和六人在鸡场打牌,去饭馆喝了啤酒,一直打到凌晨两点,他们都能作证!” 但他不知道,这场看似清晰的不在场证明,很快会被刑讯逼供彻底击碎。
第二章 炼狱逼供:“自首书” 下的血泪
马廷新的噩梦从浚县公安局审讯室开始。“他们把我两手吊起,四肢不着地,九天九夜不让合眼,要口凉水都不给。” 多年后他展示着腿窝处的疤痕,声音仍在颤抖。办案人员发明了 “上墙”“上绳”“夹手指” 等酷刑,困了就用辣椒面吹嗓子,晕了就用夹子压人中,一个月下来,他的胳膊双腿全肿了,连大便都只能在裤子里解决。
肉体折磨之外,更致命的是亲情胁迫。办案人员将妻子菅素玲抓进看守所拍了照片,又拘押了他的老父亲,拿着照片在他面前晃:“认了就放你家人,不认就一直关着!” 马廷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时,监舍里的 “号长” 袁连芳主动凑了上来 —— 这个后来在张辉张高平案中同样充当 “狱侦耳目” 的人,早已吃透案情,手写了一份长达 5 页的 “自首书”,逼着马廷新抄写。
这份伪造的供述漏洞百出:一会儿说用毛巾捂嘴杀人,一会儿说用尖刀刺颈;一会儿称死者死在立柜前,可现场勘查显示陈连荣倒在东南角小床边,柜门上的 B 型血迹与死者 O 型血完全不符。更荒唐的是,供述中 “拿走的现金”“丢弃的凶器”“更换的血衣”,警方始终未找到任何踪迹。但就是这样一份矛盾重重的 “自首书”,成了 2003 年 11 月鹤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核心证据,附带民事诉讼中,死者家属索赔 10 万余元。
开庭前,马廷新寄予希望的 6 名牌友证人,却在警方的传唤拘留中纷纷 “翻供”。有人被关押 40 多天,在威胁利诱下改口说 “记不清他是否离开”,而最初的不在场证明笔录,竟从卷宗中消失了。“那时我才明白,他们是铁了心要定我的罪。” 马廷新在庭审前的会见中对律师刘永波说。
第三章 四次审理:正义与抗诉的拉锯
一审无罪:证据链的崩塌
2003 年 12 月 15 日,鹤壁中院庭审现场,马廷新当庭翻供,扯开衣服展示伤痕:“这都是打出来的!自首书是抄的!” 辩护律师刘永波直指 18 组控方证据全是间接证据,足迹鉴定 “勉强且不科学”,凶器、血衣、现金等关键物证一概缺失,“所谓证据链全是断的”。
2004 年 7 月 23 日,一审判决传来:马廷新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法院认定,控方证据无法证实马廷新到过现场,供述与现场勘查矛盾重重,足迹鉴定亦无旁证支持。这个判决让公安机关和死者家属 “十分震惊”,鹤壁市检察院当即抗诉,称 “细节疑点不影响基本事实认定”。
发回重审:抗诉背后的压力
2004 年 12 月,河南高院开庭再审,马廷新声泪俱下地控诉刑讯细节,新委托的北京律师朱明勇当庭指出 27 处疑点:现场血迹与死者血型不符、不在场证人被胁迫翻供、袁连芳身份可疑…… 但浚县公安局纪委出具的 “无刑讯逼供” 证明,成了公诉人的挡箭牌。2006 年 8 月,河南高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理由模糊地写着 “案件复杂”。
2007 年 3 月 20 日,鹤壁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后,再次判决马廷新无罪。审判长邢天成直言:“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判无罪,是法治对人权的尊重。” 但这份判决再次引发抗诉,死者家属上诉索赔增至 16 万元,马廷新的自由又一次悬而未决。
终审裁定:迟来的清白
2008 年 3 月 29 日,河南高院终于作出终审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抗诉,一审无罪判决生效。4 月 17 日下午 3 点,鹤壁市看守所民警走进监舍:“收拾行李,回家吧,无罪释放。” 马廷新愣了半晌,抓起早已叠好的旧衣服冲出监舍 —— 此时他已被关押 1952 天,从 38 岁的壮实汉子,变成了头发花白、满身伤病的中年人。
走出看守所大门,妻子菅素玲扑上来抱住他,哭得撕心裂肺。五年间,她被辞退代课教师工作,靠打零工养活老人孩子,为上诉跑断了腿,甚至曾想过自杀。“我就知道你是清白的,一定能出来。” 菅素玲的话,让马廷新积攒五年的泪水终于决堤。
第四章 家破人亡:冤案的连锁伤害
妻子:被摧毁的人生轨迹
菅素玲的噩梦从丈夫被抓当天开始。“学校说我是‘杀人犯家属’,把我辞退了,工资都没给全。” 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患病的公公,挤在养鸡场的破棚里,鸡场因无人照料早已倒闭,欠下的饲料款压得她喘不过气。为凑律师费,她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耕牛,甚至去血站卖血换钱。
最绝望时,她收到过匿名威胁信,说 “再上诉就对孩子不客气”。有次孩子发烧到 40 度,她没钱送医,抱着孩子在雪地里哭了一夜。“我不敢告诉孩子爸爸在坐牢,只说他去外地打工了,孩子总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只能骗他们快了。” 直到马廷新出狱,10 岁的儿子才知道,那个 “打工的爸爸” 一直在监狱里。
父亲:含恨而终的等待
马廷新的父亲曾担任村支书,为人正直,却因儿子 “涉案” 受尽屈辱。被警方拘押半个月后,老人落下病根,回家后整日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念叨 “我儿是冤枉的”。2006 年冬天,老人咳血不止,临终前攥着菅素玲的手:“一定要让廷新出来,洗清冤屈。” 马廷新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出狱后在父亲坟前磕了一百个头,哭着说 “儿子不孝,让您等了这么久”。
证人:坚守正义的代价
当年为马廷新作证的 6 名村民,无一例外遭到报复。村民马海山被关押 41 天,释放后患上精神分裂症,见人就喊 “别抓我,我什么都不知道”;马建军的拖拉机被人恶意砸毁,只能外出打工躲债;最年轻的马小兵,因 “包庇罪” 被拘留后,未婚妻当场退婚,至今孤身一人。“早知道作证要遭这么大祸,我也怕,但马廷新确实没杀人,良心过不去。” 马小兵后来坦言。
第五章 赔偿与追责:正义的残缺回响
国家赔偿:迟到的微薄补偿
2008 年 5 月,在律师朱明勇的帮助下,马廷新向浚县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朱明勇提出 26 万余元赔偿诉求,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但根据当时的《国家赔偿法》,精神损害赔偿未被明确纳入。
经过多次协商,2009 年 7 月,有关部门最终核定赔偿 193852 元,按每日 99.36 元标准计算,分批次支付。拿到第一笔 2 万元时,马廷新正在鹤壁市一家小餐馆打杂,洗菜扫地每月挣 800 元。“这点钱不够还账,不够看病,但我累了,不想再争了。” 他用赔偿款还清债务,给孩子交了学费,却再也没重建养鸡场 ——“看到鸡就想起以前的日子,怕了。”
追责缺位:未被惩罚的违法者
与微薄赔偿更让马廷新寒心的,是追责的彻底缺位。尽管他当庭展示了刑讯伤痕,袁连芳承认诱导作供,证人证实被胁迫翻供,且案件存在伪造供述、隐匿证据等严重违法情形,但公开资料显示,没有任何办案人员被追究责任。浚县公安局纪委当年出具的 “无刑讯逼供” 证明,成了不了了之的挡箭牌。
“他们把我的人生毁了,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马廷新曾向有关部门举报,得到的回复始终是 “证据不足”。这种追责困境,成了诸多冤案的共同痛点 —— 正义似乎只停留在 “无罪释放”,却未能延伸到追究违法者的责任。
第六章 法治镜鉴:疑罪从无的艰难胜利
马廷新案虽未像佘祥林案那样因 “死者归来” 平反,却以 “证据不足” 两次一审无罪、终审判无罪的曲折过程,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从 “有罪推定” 向 “无罪推定” 转型的重要样本。案件中暴露的测谎结论滥用、刑讯逼供取证、证人保护缺失等问题,推动了司法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2010 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明确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确立 “疑罪从无” 原则,从法律层面杜绝了 “证据不足仍定罪” 的乱象。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例评析中指出,马廷新案的平反 “彰显了证据裁判原则的价值,是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今,59 岁的马廷新仍在鹤壁市的小餐馆打工,每天洗菜、扫地,下班回家陪妻子孩子。他的腿伤阴雨天仍会疼痛,夜里常从刑讯的噩梦中惊醒,但他很少再提过去的事。“只要家人好好的,日子能过下去就行。” 只是偶尔看到法治新闻里 “疑罪从无” 的案例,他会停下手中的活,默默看一会儿,眼里闪过复杂的光芒。
东马村的那起灭门血案,至今未破,真凶仍逍遥法外。但马廷新的 1952 天冤狱,如同一块沉重的基石,垫在了中国法治进步的道路上。那些曾经的伤痕或许难以愈合,但 “疑罪从无” 的理念,正在让更多人避免重蹈他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