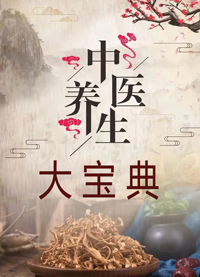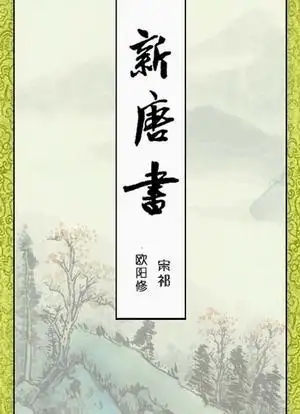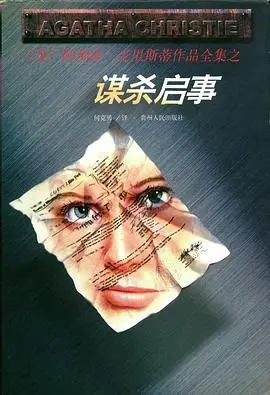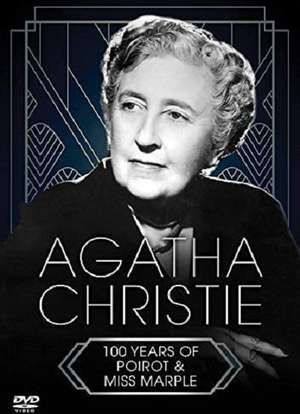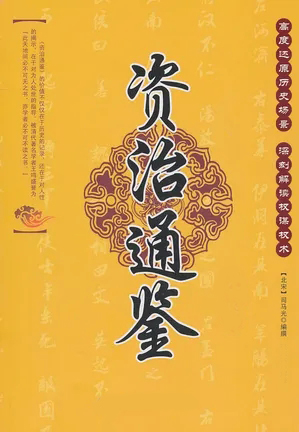王阳明《传习录》卷中 答罗整庵少宰书
【原文】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②,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注释】
①罗整庵: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明代著名理学家,对陆王、程朱均有所批评。少宰,次长,明清时侍郎一职的别称。正德十五年(1520)夏,罗整庵请假住在老家,听说时任江西巡抚的王阳明将溯赣江至赣州,就写了《与王阳明书》,在阳明经过泰和时交给他。此信即是阳明对该信的答复。
②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意为不修养品德,不讲求学问。语出《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翻译】
阳明顿首谨启:昨天幸蒙您关于《大学》的教诲,因匆忙上船,未能一一作答。今早我趁着在船上的空闲时间,又把您的信取出来拜读了一遍。我怕到江西之后,各种人事繁杂,纷至沓来,先简略地回复您,请您指正。
您在信中说道:“认识圣道固然很难,而体悟圣道则更难了。圣道确实不容易弄明白,但是学问也不能不讲。恐怕不能安于自己已有的见识,把它当作学问的最高标准吧?”
不胜荣幸!在哪里我还能听到这种教诲呢?我岂敢自以为见识已经达到了顶点而安于自己的见识呢?我正想要借助天下的有学之士来阐明圣道呢。然而多年来,听到我的学说的,嘲笑的有,非议的有,谩骂的有,置之不理、认为不屑一顾的也有,他们岂肯教导我呢?又岂肯为了教导我而反复设喻、心存忧虑恐怕来不能纠正我呢?所以,天下关爱我的人中,原本就没有谁会像您这样执着而深切,我该多么感激您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为此深感忧虑,而后世学者稍微能够传习经文训诂经典,便都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学问,不再讲求探究学问,真是可悲呀!圣道必须体悟后才能认识,而并非认识了圣道之后才下体悟圣道的功夫;圣道必须学习之后才能明白,并非在讲学之外还有明道之事。然而世间讲学的人有两类,一类用身心讲学,还有一类用口耳来讲学。用口耳来讲学的,揣测估摸,讲的是捕风捉影的东西;而用身心讲学的,言与行,学习与观察,都是确确实实求诸自己的良知。明白了这一点,就懂得了孔子的学说。
【原文】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误,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翻译】
你的来信中说我,“《大学》的旧本的恢复,是因为我提倡做学问只需在心内探求,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不免会向心外探求,于是我便废弃了朱熹分章的做法,并且删除了他增补的传注”。
我不敢这样。学习难道还会有内外的区分吗?《大学》古本是孔门流传下来的旧本,朱熹怀疑这其中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便加以改正补充。而要我说,旧本里本来就没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所以尽悉遵从旧本,仅此而已。我的过失在于过分相信孔子,而不是故意去废弃朱熹的分章且删掉他所作的传注。做学问,贵在用心体悟。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用心体会了,觉得不对,也不敢就把它当作是正确的,更何况对那些不如孔子的人所说的话呢?用心体会后认为正确,那么即使普通人说出来的话,也不敢认为是错误的,更何况是孔子说的话呢?而且《大学》旧本流传了几千年,我如今来阅读它的词语句子,仍觉得明白通顺,而其中的功夫,既简易又可行。又有什么依据能断定这段一定是在这里,那段一定是在那里,这里怎么有了缺漏,那里怎么有了错误,于是对它加以改正增补?这难道不是把背离朱熹看得过重,而把违逆孔子看得过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