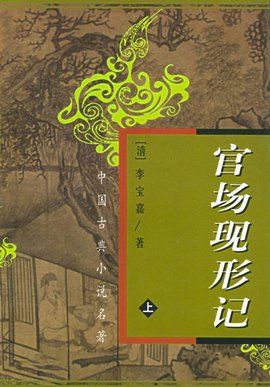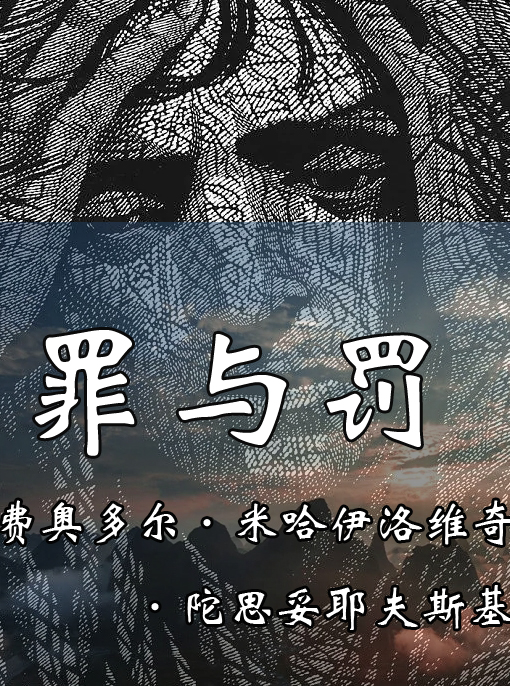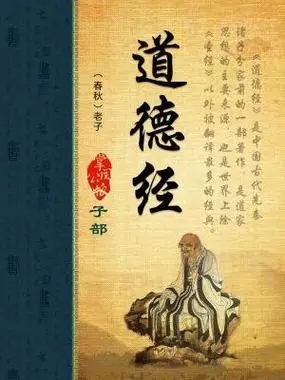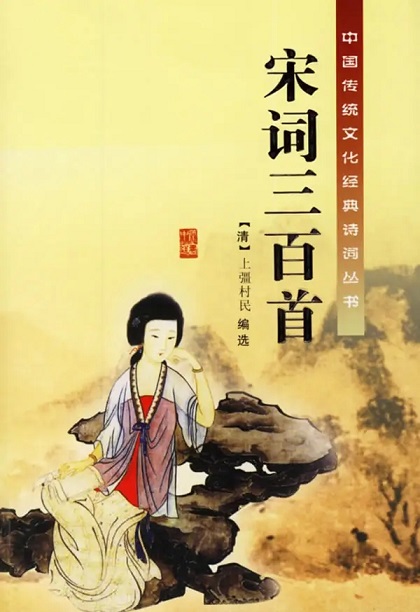【原文】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试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①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之训者,如“格于文祖”②、“有苗来格”③,是以“至”训得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加“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
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注释】
①九经:语出《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功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②格于文祖:语出《尚书·舜典》“归,格于艺典”。注曰:“归,告至文祖之庙,艺,文也。”格,至、到。文祖,尧的庙。
③有苗来格:意为有苗人到来。语出《尚书·大禹谟》:“七旬,有苗格。”
【翻译】
你来信道:“先生教人致知、明德,却又阻止他们即物就理,从事物上寻求天理。假若让懵懂昏沉的人深居端坐,不听教导和劝诫,就能够达到有了知识,德行清明的境界吗?纵然他们静坐时有所觉悟,对本性稍有领悟,那也是定慧之类的佛家的无用见识,难道果真可以通晓古今、通达事变,对治理国家有实际作用吗?你说:‘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这些话虽然显得高超而独到,不墨守陈见,但恐怕和圣道不大吻合吧?”
我所讲的格物致知,正是为了穷尽事物,我未曾禁止人们穷尽事理,让他们深居静坐,无所事事。如果把即物穷理讲成是前面所说的重视外在知识,忽略内心修养,那也是错误的。糊涂的人,如果能够在万物之上精察心中的天理,发现原有的良知,那么即使愚蠢也定能变得聪明,即使柔弱定能变得刚强。最后就能够行达道、立大本,九经之类的书也能一以贯之没有纰漏,难道还需担心他会没有经世致用的实际才干吗?那些只谈空虚寂静的佛、道弟子,恰恰是不能在万事万物上精察心中的天理,发现其心中本有的良知,以致抛弃人间伦常,把寂灭虚无当作是正常现象,所以他们才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谁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说也会有这样的弊病呢?
身体的主宰是心,心的虚灵明觉就是人原本的良知。虚灵明觉的良知因感应发生作用,就是意念。有识即是有意,无识即无意。怎么能说认识不是意念的本体?意念的运用,一定会有相应的东西,就是事。如果意念在侍奉双亲上起作用,那么,侍奉双亲便是一件事;意念在治理百姓上起作用,治理百姓便是一件事;意念在读书上起作用,那么读书就是一件事;意念在听讼上起作用,听讼也就是一件事。只要是意念起作用的地方,就有事物存在。有这个意就有这个物,没有这个意也就没有这个物,事物难道不是意念的运用吗?
“格”的含义,有用“至”字来训释的,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里的“格”,都是“至”来解释的。然而“格于文祖”,必定诚心诚意地纯然至孝,对于人间和阴间的道理都无一不晓,之后才能叫作“格”。苗人只有通过礼乐把他们教化之后才能“格”,所以这个“格”也有“正”的意思,不能够仅仅用“至”字就能完全解释它的含义。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中的“格”,都是“纠正不正以达到正”的意思,不能用“至”字来训释。那么《大学》中“格物”的解释,怎么知道它不是用“正”字而须用“至”字来解释呢?如果用“至”字来训释,就必须用“穷至事物之理”才说得通。用功的要领全在一个“穷”字,用功的对象全在一个“理”字上。如果在前面把“穷”字去掉,后面把“理”字去掉,而直接说成“致知在至物”,这说得通吗?“穷理尽性”是圣人既定的教诲,在《易经》里已经有了记载。如果格物的含义真的就是穷理,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却一定要让语意有了转折且不完整,说这种话,造成后世的弊病呢?
《大学》里的“格物”和《易经》里的“穷理”,意思只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含义基本上是一样的。穷理里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功夫。所以谈到穷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功夫就已经都包含在其中了。谈到格物,就必然一同有致知、诚意、正心,这样,格物的功夫才能够是完整的。现在说到格物便说成是穷理,就只是把穷理当作了一种认识,而不认为格物里还包括实践了。这样,不但没有把握到格物的宗旨,就连穷理的本义也是一并丢掉了的。这就是后世的学者们,把认识、实践分而为二,并且让它日益支离破碎,圣学日渐残缺晦涩的原因所在。你承袭旧来的观点也在所难免,而觉得我的学说与圣道不符,这也不算什么。
【原文】
来书云:“谓致知之功,将如何为温凊、如何为奉养即是诚意,非别有所谓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宁复有可通乎?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凊、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知如何而为温凊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凊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温凊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其于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凊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温凊之物格,然后知温凊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
故曰:“物格而后知至。”①致其知温凊之良知,而后温凊之意始诚;致其知奉养之良知,而后奉养之意始诚。故曰“知至而后意诚”。此区区诚意、致知、格物之说盖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将亦无可疑者矣。
【注释】
①物格而后知至:语出《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翻译】
你信中说:“先生您所说的致知的功夫,是要保证父母的冬暖夏凉,怎样去奉养父母的诚意,而并非另有个什么格物,我想这恐怕不对吧。”
你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揣度我的观点才这样说的,并不是我这样跟你说过。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难道还有能讲得通的地方吗?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想让父母冬暖夏凉、想要侍奉父母,这只是所谓的意,而并不能把它当作诚意;一定是要笃行了让父母冬暖夏凉、侍奉他们的愿望,务必是自己在做的时候感到满意,没有违心,这样才能叫作诚意。知道如何让父母冬暖夏凉的礼节、知道怎样适宜地侍奉父母,只是所谓的知,而不能说已经是致知;必须知道了,并且切实完成所知道的礼节,才能称作致知。使父母冬暖夏凉的事,对父母奉养适宜的事,都只能算作是事物,而不能算作是格物;在父母冬暖夏凉和侍奉适宜的事情上,必须遵循自己的良知去做,而没有丝毫不到的地方,才叫作格物。父母冬暖夏凉的物“格”了,使父母冬暖夏凉的良知才是“致”了;奉养父母适宜的物“格”了,很好地侍奉父母的良知才算是“致”了。
所以《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有了让父母冬暖夏凉的良知,才能产生使父母冬暖夏凉的真诚的意念;有了适宜奉养的良知,才能产生奉养适宜的真诚的意念。所以《大学》说“知至而后意诚”。我说的诚意、致知、格物的学说大概就是这样。你再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原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①。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②,小杖、大杖③,割股④、庐墓⑤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⑥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真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真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真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哽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⑦,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注释】
①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语出《中庸》“君子之道费而稳。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②养志、养口:典出《孟子·离娄上》。
③小杖、大杖:典出《孔子家语·六本》。曾子在瓜地锄草时,锄掉了瓜苗。其父大怒,用大杖将其打昏在地。曾子醒来后,先向父亲请安,又回到屋里弹琴,使父亲知道自己安然无恙。孔子知道后很生气,教育曾子应像大舜侍奉父亲那样,父亲用小杖打时则坦然承受,用大杖打时就逃跑,以免使自己身体受伤,使父亲背上不义的罪名。
④割股: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介子推曾割大腿上的肉给文公吃。后以割股治疗父母之病为至孝。
⑤庐墓:古时,父母亡故后,孝子在墓旁搭建草棚,一般要住三年,以表达对父母的哀思怀念之情。
⑥“道在迩”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上》。
⑦为无后:语出《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翻译】
你来信写道:“圣道的宗旨很容易明白,就像先生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具体的细节,随着时间的变化,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需要学习之后才能明白。谈论孝道就是温凊定省这些礼节,现在谁不明白?至于舜不请示父母就娶妻,武王还没有安葬文王便兴师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疗亲,为亲人守墓三年等事情,可能正常,可能不正常,这是处于过分与不足之间。必须讨论个是非曲直,作为处事的原则。然后人的心体没有遮蔽,这样临事才能没有过失。”
“圣道的宗旨很容易明白”,这句话是对的。只是后世的学者们往往忽略那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不去遵循,却去追求那些很难明白的东西,这正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圣道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明白吗?人们的毛病在于不去遵循罢了。”愚夫愚妇和圣人是同样拥有良知良能的。只是圣人能够意识并保存自己的良知,而愚夫愚妇则不能,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节目时变”,圣人对此岂有不知的?只是不一味地在这上面做文章罢了。圣人的学问,与后世所说的学问不同,它只是意识并保存自己的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你不去保存自己的良知,而是念念不忘这些细节,这正是将那些难于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病了。良知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具体细节,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具体细节随时间变化也不能够事先预测。因此,规矩尺度一旦确立,那么方圆长短就能够一目了然了,而天下的方圆长短也就用不完了。确实已经达到了致良知的境界,那么具体细节随时间的变化也就一览无余,天下不断变化的细节就能应付自如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在我们本心的良知上的细微处去体察,那你怎么去应用你所学的东西呢?这是不依照规矩尺度想去确定天下的方圆长短。这种狂妄的说法,只会每天徒劳而一无所成。
你说“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真正知道的人很少。如果说简单地知道一些温凊定省的礼节,便能认为他已经做到了致孝的良知。那么凡是那些知道应当仁爱百姓的国君,都能认为他能够致仁爱的良知;凡是知道应当忠诚的臣子,都能认为他能致忠诚的良知,那么天下哪个不是能够致良知的人呢?由此便明显可见,“致知”必须实践,没有实践便不能够称他能够“致知”。这样知行合一的概念,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舜不告知父母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便已经有了不告而娶的准则,所以舜能够考证某部经典或者询问于某人才这样做的吗?还是他依照心中的良知,权衡利弊轻重,不得已才这样做?周武王没有安葬文王便兴师伐纣,难道是武王之前便已经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准则,所以武王能够考证某部经典或者询问某人才这样做的吗?抑或是他依照自己心中的良知,权衡利弊,不得已才这样做?如果舜并非担心没有后代,武王并非急于拯救百姓,那么,舜不禀报父母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便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后世的人不努力致其良知,不在处理事情上精细地体察天理,只顾空口谈论这中间时常变化的事物,并执着于此作为处理事情的准则,以求得遇事时没有过失,这也差得太远了。其余几件事也能够依此类推,那么古人致良知的学问就可以明白了。
【原文】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①‘前言往行’②‘好古敏求’③‘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④‘好问好察’⑤,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⑥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注释】
①多闻多见:意为通过多闻多见增长知识。语出《论语·为政》。
②前言往行:语出《周易·大畜》卦辞“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为君子应该多了解古代前贤的言行,以积蓄自己的德性。
③好古敏求:意为喜欢古学而勉力追求。语出《论语·述而》。
④博学详说:语出《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为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等到融会贯通之后,再回头来简略地叙述其精髓大义。
⑤好问好察:意为喜欢请教别人,并且喜欢体察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以便能了解民意。语出《中庸》。
⑥“盖有”二句:语出《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翻译】
你来信中说:“您说《大学》里格物的学说,唯指寻求本心,还勉强说得通。至于《六经》《四书》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等,都是指在处事和辩论之中得到的,用功的内容和次序是不能弄乱和改变的。”
格物的含义,之前我都已经详细地谈过,你仍觉牵强,想必也不需要我再多加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是孔子针对子张说的。子张好高骛远,只以多闻多见当作学问,而不能认真存养本心,所以心存疑惑,语言和行为里便难免有埋怨和悔恨,而他所谓的见闻,又恰恰滋长了他好高骛远的心性。所以孔子大概是为了纠正他多闻多见的毛病,而并非把多闻多见当作做学问。孔子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就像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意思差不多。这话正好说明明德行的良知并不是从见闻中来的。孔子所说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门从见闻的细枝末节中探求,是第二位的事情罢了,所以他又说“知之次也”。把见闻的知识当作是次要的学问,那么学问之首是指什么呢?从此处,对圣人致知用功的地方我们可以完全窥见了。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如果果真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为何说这种话来欺骗子贡呢?一以贯之,不是致良知是什么?《易经》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积蓄德性为主,而更多地了解前人言行的人,不也是在做积蓄德性的事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好古求敏”,就是热衷于古人的学说并且勤奋敏捷地探求心中的理。心即是理,学习就是学习本心,探求就是探求本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好古并不是像后世那样,广泛地背诵记忆古人的言辞,心中却念念不忘追求功名利禄等外在的东西。“博学审问”,前面也提及过。“温故知新”,朱熹也把它当作是尊德性的范畴。德性难道能从心外求得吗?知新必经由温故,温故才可知新,这又可作为知行并非两回事的有力证据。“博学而详说之”,是为了再返回至简约,如果不是为了返回至简约,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什么呢?舜好问好察,仅仅是中正平和地达到至精至纯合乎道心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过实践、废弃过辩说呢?但是实践和辩说的时候,都要知道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致其本心的良知,而不是像后世学者那样只在口耳里空谈便当作认识了,把知行分而为二,才会产生用功有先后区分的说法。
【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①,乡原②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③,汤、武、楚项之放伐④,周公、莽、操之摄辅⑤,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常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⑥,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⑦,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注释】
①杨、墨之为仁义:杨,即杨朱,字子居,又称阳生,战国时魏人,主张为我,近似于义。墨,即墨翟,战国时鲁人,墨家的创始人,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近似于仁。
②乡原:指不讲原则、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
③尧、舜、子之之禅让:古代部落首领的职位传贤不传子,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子之为战国时燕王哙的相国,后哙让位于子之,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④汤、武、楚项之放伐:商汤放逐夏桀于南巢,周武王讨伐商纣于牧野,项羽杀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
⑤周公、莽、操之摄辅:周公在周成王年幼时摄政,待成王成年后还政于成王,为后世典范,事见《史记·周本纪》。王莽以外戚居大司马,杀汉平帝,立孺子婴,自摄其政,后篡位,改国号新,事见《汉书·王莽传》。曹操讨伐董卓,迎立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废献帝,建魏国,事见《三国志·魏志》。
⑥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汉武帝时曾与大臣们议论立明堂之事,武则天曾毁乾元殿而立明堂。
⑦泮宫:西周时诸侯设立的学校。
【翻译】
你来信说:“杨朱、墨子的仁与义,乡愿的破坏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戮,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情都无从考证,我们将从何去听信呢?而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还未考察识别,假如国家想要兴建明堂、建立学校、制定历律、操办封禅大典,又将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论语》中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也’。这可以被当作定论了。”
你提到的杨朱、墨翟、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之间的区别,就跟前面所说的舜和武王的情况大致相同,可以类推。古今事变的问题,前面在谈到良知的学说时,已经有了规矩尺度作为比喻,因此也无须多说了。
至于兴建明堂、建立学校等事,似乎不谈一谈还不行。但是说来话长,姑且就你提到的这些事情来加以辨析吧,你的困惑也能够稍微减少一点。明堂、学校的制度,最早在《吕氏春秋》的《月令》篇和汉代儒生的注释中出现,六经、四书里没有详细提到。难道吕不韦、汉代儒生的知识比三代圣贤的知识还要好吗?齐宣王时期,明堂尚且存留有未被毁掉的,那么幽王、厉王时,周王朝的明堂都应该是安然无恙的。尧舜时以茅草盖屋,以土为台阶,明堂之制还没有完备,但并不妨碍他们治理天下。幽王、厉王时的明堂,沿袭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旧制,但对于乱世也无补于世。为什么呢?这不是正好可以说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使是茅屋和土台阶,也仍旧是明堂,用幽王、厉王的心来行幽王、厉王的暴政,虽然有明堂的设立,也不过是他们施行暴政的地方?汉武帝重新探讨过立明堂的事,武则天也曾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泮宫,都以地形来命名。然而夏商周三代时的学校,都是以教育伦理纲常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看它的外表像不像璧环或者它是不是建造在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