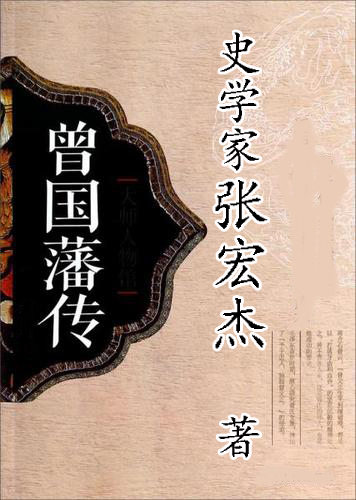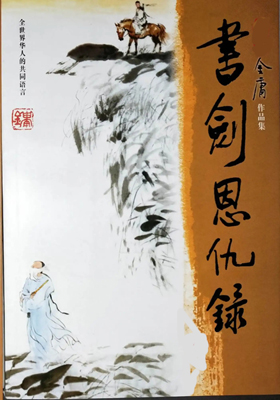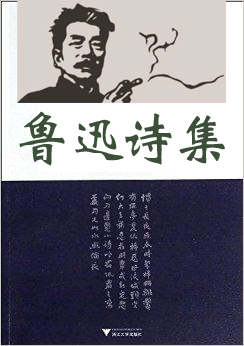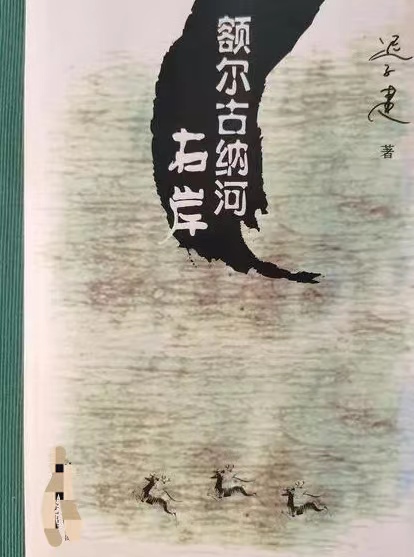王阳明《传习录》卷中 答顾东桥书
【原文】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①,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注释】
①“故先生”一句:王阳明早期曾强调“诚意”的重要性,他所著的《大学古本序》第一句就是“《大学》之要,诚意而已也矣”。
【翻译】
来信写道:“近代的学者,注重外在的知识积累而忽视了内在本心的存养,知识广博却遗漏了关键所在。所以先生特意提倡‘诚意’,以针砭时弊,这实在是很大的恩德呀!”
你对时弊洞若观火,那你又打算如何去拯救呢?我的思想观点,你的几句话都已经把它说明白了,我能再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诚意”的学说,原本是孔门教人用功的第一要义,但近代学者却把它当作次要看待,所以并非是我本人的首倡,我只是稍稍把它的重要性提示出来。
【原文】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①、定慧顿悟②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突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注释】
①明心见性:佛教禅宗的主张,意为让自己心底清澈明亮,待看见自己的真性,就可以成佛,而无须于文字上抠求。
②定慧顿悟:定慧,佛教的修养功夫,指禅定与智慧。除去心中的杂念为定,明了事物的道理为慧。顿悟,意为突然之间明白了困惑已久的佛理,一悟成佛。与儒家的“困知”相对。
【翻译】
你来信说:“担心先生的学说立论太高,而学生们用功时又过于简单,难免会产生谬误,就容易陷入佛教中的明心见性、定慧顿悟,这就难怪世人会对先生的学说产生怀疑。”
这些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说,是就学者的本心而言,学者的本心需在日常事物中体察、探究、实践、落实,实实在在用功,这其间分很多阶段、也有很多积累!它和佛教的定慧顿悟的说法正好相反。听到我的学说的人自己可能没有圣人的志向,加上又没有详细研究过我的学说,所以有些疑惑,也不足为怪。但是凭你的聪明,对我的学说应该是一点就明,为什么也要说“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呢?
【原文】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①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注释】
①近闻:指朱熹的知先行后的观点。
【翻译】
你来信说:“你说知行应该同时进行,不应该区分先后,也就是《中庸》中的‘尊德行而道问学’,两种功夫互相存养,互相促进,内外本末,不能分割,只能一以贯之。但是修行功夫不可能没有先后阶段的区别,就像知道是食物才吃,知道是汤水才喝,知道是衣服才穿,知道是路才在上面走。不可能还没见到是什么东西就先行事的。当然,在先后的顺序间也只是瞬间,并非有截然的区分,不会是今天知道了这件事,明天才去行事。”
你既然已经说“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了,就应知道知行并举的说法,根本就不用再去怀疑了又还说“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这不是已经自相矛盾吗?“知食乃食”等说法,尤其明白易见。但是你被朱熹先生的观点所蒙蔽,自己还没有察觉而已。人一定是先有想吃东西的心,之后才会去认识食物,想吃食物的心就是意,也是行动的开端。而食物味道的好坏,必须等到入口才能知道,难道在还没有进口之前就会预先知道食物味道的好坏的吗?必定是先有走路的想法,之后才会去认识路,想走路的心就是意,也就是走路的开端。而路途的坦荡或是险峻,也须等亲自去经历过之后才会知道,难道在还没有亲自走过就预先已经知道路途是坦荡或险峻的吗?“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也跟吃食、行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如果像你所说的,就是所谓的“不见是物而先有事”了。你又说“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也只是因为你洞察得还不够精确罢了。但是,即使像你所说的那样,知行并举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原文】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①,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注释】
①告子义外之说:语出《孟子·告子上》:“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的评论见《孟子·公孙丑上》:“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翻译】
你来信道:“真正的理论是能够指导实践的,而不实践就不足以称为认识。向学者指出的切实的方法,让学者们务必躬身实行,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把实践当作认识,恐怕人们只会专门追求存养本心,而遗漏了万物之理,也肯定会有偏颇不通的地方,难道这是圣学关于知行并举的方法吗?”
认知确切之后付诸行动就是实践,行事实践之后明确的体察就是认识。知行的功夫本来不能分离,只是后世学者要把它们分开作为两部分来用功,反而丢失了知行的本体,所以之后才会有知行并举的说法。真知是能够指导实践的,不实践就不足以称为认识。像你的来信信中所说“知食乃食”等,已经能够明白了,前面也已经大略说过了。这虽然是因为拯救时弊才说出来的,但是知行的本体就是这样的,并非是我为了追求一时的效用,而按照自己有所褒贬的意思提出来的。
专门追求存养本心,便抛弃了万物之理,大概这是失去本心的一种表现。万物之理并不存在于心外,在心外探求万物之理,就是没有万物之理;遗漏万物之理而追求存养自己的本心,那么本心又是何物呢?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即是理。所以拥有孝心就是有孝顺父母的道理,没有孝心也不存在孝顺父母的道理了;有忠心就有侍奉君王的道理,没有忠心也就没有侍奉君王的道理了。理难道是在我们的本心之外的吗?朱熹先生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像他这样把心和理先分开之后再结合起来,未免就会产生让学者们把心与理分开看待的弊端。后人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的忧患,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心就是理。在心外寻求万物之理,实际上是告子的“义外”观点,会有偏颇不通的地方,孟子也因此批判告子不懂得义。心,唯有一个,就它对所有人的恻隐而言就是“仁”,就它的合理而言就是“义”,就它的条理清晰而言就是“理”。不能在心外求仁、也不能在心外求义,难道就独独可以在心外求理吗?在心外求理,是把知行当作两件事了。在我们的心里寻求理,这才是圣学知行合一的教诲,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特别提示:感谢阅读!若本文能为您带来一丝启发或一刻美好,请分享转发给身边的人,既是对我们的支持。传播正能量,我们携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