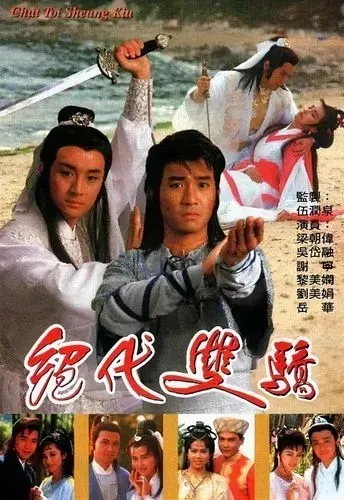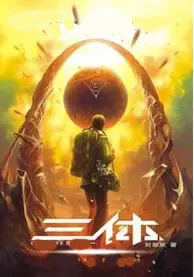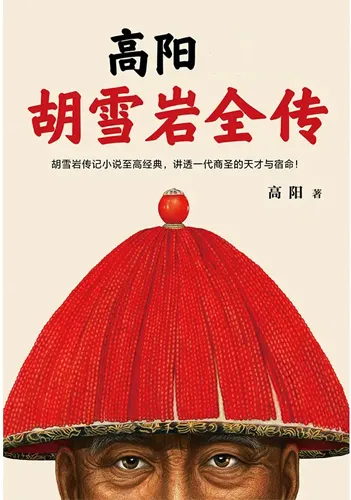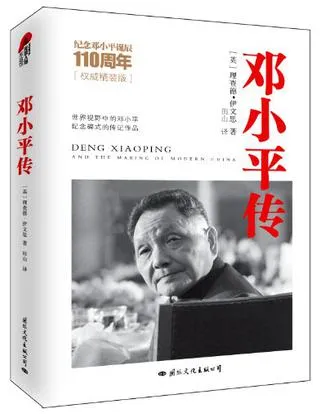我对着那张封条又看了一眼,然后从人群中悄悄的退了出来,后面的一节课,我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中,但表面上又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在刚才课间休息的时候,一群高年级学生涌进了老师办公室,把老师们的办公桌和柜子一一贴上了封条。
我是听到人声喧哗赶去看热闹的,到了现场却不知不觉融入其中,无动于衷?除非你不是人。但我又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于是悄悄的拿了一张封条,贴在了教导主任班主任老师楼zhufeng的办公桌左边下方的柜门上,那里是唯一还没有被贴的地方。
如果是一个调皮捣蛋成绩又不好的坏学生,大家不会感到奇怪,但这事竟然是我干的,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
事情还得从上个学期,1966年上半年,四年级下开始说起,那时我被班主任楼老师任命为少先队中队委员。一个班级是一个中队,中队委员有五人,正副中队长各一人,还有学习委员和劳动委员,我是墙报委员,负责少先队墙报。中队下面有四个小队,有正副小队长各一人。整个学校设一个大队,和中队一样也是五个委员。
......
还是再往前挪挪,不然说不清楚。

1965年寒假,我离开了平津桥2号,搬到了离吴山不远的通江桥附近,离原来的家大概1.5公里。去办转学手续时,柳翠井巷小学的班主任陈老师极力挽留我,她不想失去一个受到过全校表彰的好学生。但我作为一个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学生(好像今天还是不懂),对于转学去新学校异常的兴奋,铁了心的要转学,而大人们也怕路远不方便不放心,于是老师只好放行。小孩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之前一次生病住院,办住院手续时我都兴奋的手舞足蹈。
到了抚宁巷小学,报到的地方是在新教学楼后面操场边的一个大屋顶房子里,看上去以前是个庙,被学校改成了大礼堂。当年很多学校都是利用了以前的庙宇建筑,柳翠井巷小学也是一个庙。
只有一个老师在里面,她翻看了我的材料后说,你在原来学校是三(1)班的,按理应该还是转入这里的三(1)班,但我想把你转到我的班里来。于是我就成了三(2)班的学生,班主任就是楼zhufeng,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校长王乐学,就她说了算。
楼老师一头短发,看上去就是精明能干的女强人,语速很快声音洪亮,估计当时也就30多岁吧。
不久我就发现,楼老师哪都好,就一个问题,重女轻男,而且是极度的重女轻男,极度到了有点变态的程度。她对男生的缺点一丁一点都无法容忍,哪个男生上课不认真听讲做小动作或者被别的老师投诉,一定会在课堂上被她声嘶力竭骂的狗血喷头。
更要命的是,她经常会在下午放学时板着脸走进教室,冷冷的扫视一遍全班同学,然后一字一顿的说:“全体女生可以放学了”,等女生们全部离开后,稍停片刻,又说:“张晋浙和陈向明可以走了”。等我们俩从教室后门溜出去刚关上门,里面就火力全开吼声震天地动山摇了。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次墙角。
到此为止,我和楼老师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在所有老师眼中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但是么,人总是有虚荣心的,小学生也是人。虽然楼老师给了我女生同等的待遇,虽然她经常表扬我,但有一件事却始终是口惠而实不至,就是......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就是三个学期都快过去了,却始终没有给我个一官半职。如果还留在老学校,我早已是一条杠了,两条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搞不好都混成三条杠了,而在这里我啥也不是,我当时都有点后悔转学了。
五个中队委员全是女生,八个小队长只有两个男生,谁说妇女只能顶半边天的?在柳翠井巷小学,要不是因为年龄偏小不够入队条件,拖到三年级上才入队,我肯定已经有个一官半职了。
十年媳妇熬成婆,转机终于来了。四年级下半学期快结束时,因为六年级要毕业了,毕业后大队委员就出现了空缺,我们班的中队长韩jin’e被增选为大队委员,于是我就直接跳过小队这一级成了中队委员。本来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我做梦都梦见自己袖子上挂着两条杠,街上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眼神。
可是,俗话怎么说来着?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平地一声惊雷,炸碎了我的梦想。1965年6月1日,(还挑了个六一儿童节,就不能等到八一建军节吗?),中央军委宣布取消军衔制。军衔制突出了等级观念,是封资修的东西,破环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少先队立马跟上,宣布取消少先队干部的袖标。到嘴的鸭子飞了,你说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遗憾,委屈,想哭......说不出的感觉......
其实作为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和不满,只是略微有一点点失望。
直到那个喧嚣的下午,直到高年级学生冲进老师办公室的那一刻,,,身处那样的环境中,我内心深处,之前连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那么一丁点的失望,抑或是不满,被迅速放大放大再放大,几乎是要演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整个人就变得冲动起来,于是奋不顾身的拿起了封条,即使明知这样的后果是老师会很生气很生气。虽然我没有留下署名,虽然我自认为是悄悄的贴上去的。但楼老师竟然还是知道了,有人打了小报告。革命队伍中内奸无处不在,我被人出卖了。(后来在高中时,在工作单位里,我经常被人打小报告。)
(反思那一段历史,主流思维还停留在所谓的善恶之间,简单的把一类人归为“恶人”,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人”,就不会发生那么多邪恶的事情,恨不得倒回去一千年诛恶人九族。)
1967年2月5日,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又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到来了。
1967年11月,北京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成立红小兵,上海斜土路小学率先响应,12月22日中央同意全国范围取消少先队成立红小兵。
1966年9月五年级第一学期,恰逢停课闹革命,大学关门不招生,中学也不招生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六年级毕业生没有地方去,只好留在小学里,人们称之为七年级戴帽生。当时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反正不上课闲的没事干,大家经常上街瞎逛。以前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都是从大字报里知道的。从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江李曹、、、一直打到每个单位的大大小小领导,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小小年纪就认识了众多名人名家。
我才五年级,对学习以外的事自然是一窍不通,但那些七年级的学生们显然就比我们成熟了不止一点点,他们在酝酿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还想去全国大串联。而我因为和院子里一个七年级的同学关系比较好,成为第一个被拉进去的五年级学生。
从最初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清华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战斗队、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黑一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到省里市里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满大街都是绿军装红袖章,走在大街上不穿件绿军装戴个红袖章,就像如今没有LV包包没有手机一样,没脸出门了。
杭州也和北京一样,有一个黑一司和红三司(杭州市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兵)。红一司之所以后来被称为黑一司,是因为他们都是保皇派,失势了,而且巧的是,他们的红袖章上面的字是黑色的,其他所有组织都是黄色的字。

没多久,七年级的学生们搞出一个“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选举了司令、常委,记得有许shuijin、康yunchi两个司令,其他都忘了,当时就一直没熟过。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夺权,,,结果么,呵呵,连老师办公室都没拿下,只占领了校广播室和几间教室。我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在一起,从家里搬来被褥,第一次在学校过起了集体生活,不过吃饭还是要各回各家的。后来,我这个以往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好学生,竟然和一个革命战友发生了一场斗殴,一气之下我卷起铺盖回家当逍遥派去了。革命斗争果然能锻炼人,刚进初中那会,我又和同学打过几次架,和同班打赢两次(比较文明,未造成伤害),打平一次,和外班打输一次(小输,无伤大雅)。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出手的理由。
在学校闹革命其实挺无聊的,成天无所事事。第一次在广播室遇到扩音机和电唱机,知道了扩音机要先开低压再开高压,关机时要先关高压再关低压。没事放几张唱片,都是语录歌。一次一个同学误放了国歌,体育老师赵某火速赶来制止,“田汉作词的也敢放?”放乐曲可以,有歌词是不能的。
期间也发生过一件令人紧张的事。两位司令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情报,说有人要攻打我们学校,于是和平安里小学的“怒海轻骑战斗队”成立联盟,有事互相支援。一天,许司令找到我,让我立刻和另一个同学去平安里小学求援,说是“敌人”马上要来了。等我们两人一路小跑气喘吁吁赶到平安里小学,发现怒海轻骑战斗队没什么人在,说是已经接到消息过去了。等我们回到学校,发现他们来了几十个人,年纪大一点的头戴藤帽(当年的安全帽是柳条藤编织的),手握铁棍,从西边楼梯上去,东边楼梯下来,绕行一圈,边走边用铁棍往地上砸,敲的大楼咚咚咚响。敌人始终没有现身,八成是被吓跑了。
无事生非,这话一点不错。一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单位,借我们学校教室开会,门口停了一排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就好比如今的奔驰宝马。有个高年级同学经常乘别人自行车忘记锁了,偷偷骑上去过一把瘾。就像你刚学会开车,手特别痒。这次又故技重施,但每辆车都上了锁。他不死心,找来半块砖头,对着一辆车锁的搬手敲了三下,锁开了。经验丰富的惯犯。然后他带上我,沿江城路骑到城站兜了一圈。不料就这么点功夫,人家会议已经结束了。等我们回来时,一群人在校门口吵吵,被抓了个现行。好在当年人们的法治意识淡薄,更没有什么维权索赔的概念,数落了几句就万事大吉了。
戴帽子的七年级八年级,这些超龄小学生里还是有一些社交能力超群的人物,许司令算一个。在他的操作下,带一帮人搞串联去了一趟上海。当时各地都有接待站,只要是串联的红卫兵来了,白吃白喝白住不要钱,火车汽车也不要钱。我因为大人不放行,很遗憾没能去成。第二年,正当许司令雄心勃勃想去北京时,中央命令停止大串联。
许司令还联合其他小学积极活动,想参和大人们的事,加入红三司,最后搞到一个番号,“杭州市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兵(少年部)”。不过这个所谓少年部当年并没有什么战果,大人们只不过是为了不打击孩子们的革命积极性,糊弄一下而已,毕竟人性再恶,还没有恶到利用一帮天真无知的孩童的地步。

(两块造反总部的红袖章还在,也许有一天可以成为文物吧。)
大家又在学校里折腾了一阵,最后还是作鸟兽散。接下来要复课闹革命了。
最后一次见到楼老师,记不得是哪一年了。那天我刚翻过通江桥,向鼓楼方向走去,就见远处过来一个老太婆,腰弯的非常厉害,因为背着一个年纪很大的男孩,看上去有九岁或十岁或者更大点,反正觉得这个男孩挺沉的,所以老太婆腰弯的特别厉害,很吃力的样子。因为觉得这么大的孩子还要背,挺怪异的,所以我的视线一直停留在他们身上。但因为老太婆低着头,我看不清脸,只是看到她头发有点点花白。当我和她擦肩而过时,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年纪并不大,皱纹也不多,,,。继续走了两三步后,我猛然转回身望去,心头感到无比的震撼,这,刚才过去的不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楼老师么?当年英姿飒爽的她,怎么也和今天的形象对不上号,我想喊一声楼老师,张了张口,终于还是闭上。
我想起当年在课堂上,她激昂的说,我改名字了,珠啊凤啊的太俗气了,我要学秋瑾,改名叫楼瑾。
来源:老张讲故事,作者:张晋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