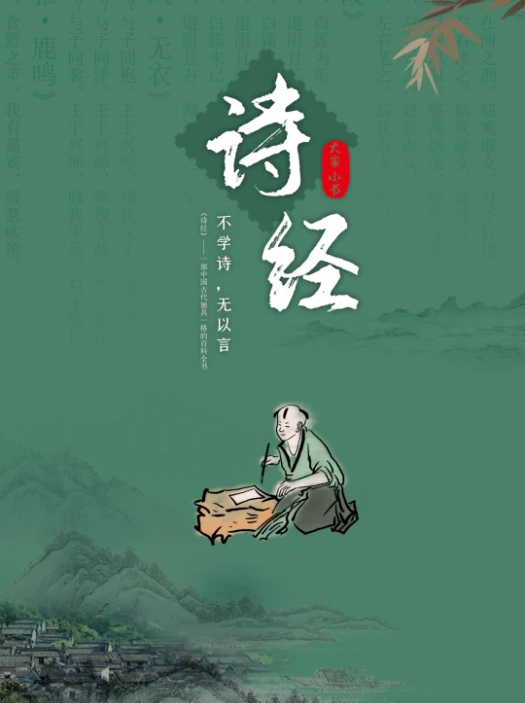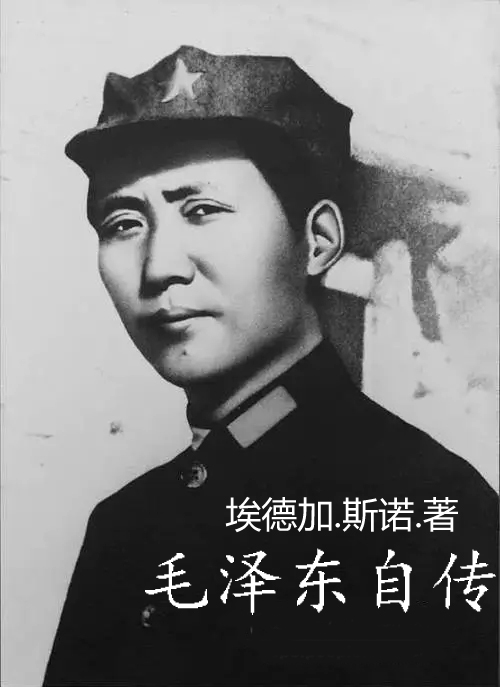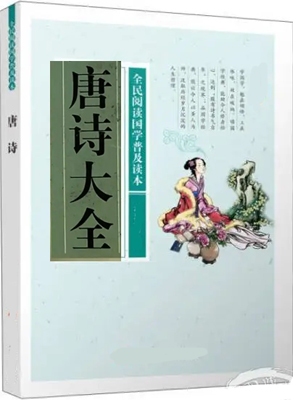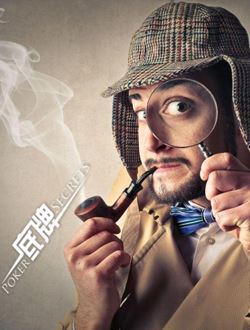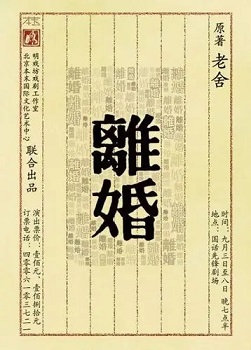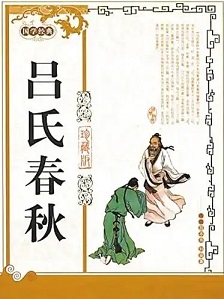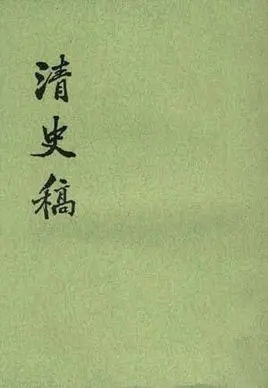下面其实是笔者的一个历史背景叙事,笔者希望相关人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都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点口述。你可以不把它当反思,更不把它视作忏悔,纯粹就是提供个人史料。当然,既然是个人史料,必定会有倾向、有选择、有偏颇。换言之,每个人都是一段历史,每个人的历史一定会与其他人有重合、有交叉、有并进、有逆行。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人在历史长河里一朵小浪花。它不起眼,但无数朵小浪花就能汇成巨浪的形象。例如笔者下面所述,作为个人的经历与体验,肯定会有偏颇,而且也一定与其他人的体验会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但笔者在回叙中,即使挂一漏万,但所挂之一肯定是真实的,绝无虚构,更不会任意地造谣抹黑,撒谎污蔑。因此,笔者真诚地欢迎读者对本文叙事进行监督检查,如本质处有所失实(不包括像作品名称记忆失误这种非本质性问题)笔者将全网道歉。另外,本文作为个人口述史只提供给大家作参考甚或消遣,并不强制或诱导他人接受,更不作为他人对史实评价的依据。
本人出生于医护人员家庭。父亲贫农成份,在一个偏僻的山乡与我的奶奶相依为命;母亲地主成份,却于14岁便脱离家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两人考上当时金华地区赫赫有名的金华卫校,毕业后一起分配到东阳县(1988年5月撤县设市)卫生系统。父母虽非共产党员,然一生勤勤恳恳,脚踏实地;虽无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已各尽己之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可以说,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工作的尊重,对同事的热情……成为我一生的榜样。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父母不惹事,也不怕事;我不怕事,但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也就是说,只要必须,我会主动惹事!包括反对组织老师编卖资料、大量招资助生(计划外学生)等。这也正是笔者教书前十年在各种评优评职称中不断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只不过本人没消沉下去,而是越挫越勇。
1967年9月,笔者7岁,读小学;1977年7月,笔者17岁,高中毕业。这意味着整个特殊时期,笔者都在念书。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都教育我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公无私,破旧立新”“新三年、旧三岁、缝缝补补又三年”“劳动光荣”“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那时候的我们具有很强的民族荣誉感、集体精神、英雄理想。
当然,读小学时,也跟着几个大孩子干过一些荒唐事:去田埂摘毛豆,去山上摘毛桃,到桑田采桑椹,下水塘抓鱼虾等等。但若被父母知道,也少不了一顿骂。我们都知道,那不是捡,而是偷。被农民追赶,会心有余悸,但绝不会痛骂追赶的农民是凶神恶煞。记忆中,还干过所谓的坏事,就是一群小屁孩,捏着用两张废票拼接而成的假电影票,遛进电影院里看《闪闪的红星》《青松岭》《杜鹃山》,而且孩子们“作案”多起,一次都未被抓。以为自己作案手段有多高明,后来才知道是检票的大人们有意放水。他们说爱看电影的孩子都不坏!
那个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初高中四年,每年寒暑假分别要背铺盖去农村或工厂劳动一二周(史称接受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老师跟我们一起打地铺,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有时候还有拾粪任务。那时候,我们所谓的居民户口的孩子比农村户口的孩子干更多的农活。而我虽然先天营养不良,但却能筋骨强健,毫无骄娇之气,与每年差不多一个月的高强度劳动是分不开的。
同时,我们对老师是十分敬畏的,笔者除了高一时,与班主任因赛诗结下的“梁子”而在“庆祝'文*'胜利十周年”会后的游行中吵了一架外,对所有老师,几乎都是言听计从,对他们的批评更是不敢回怼的。1977年,毕业前夕,教语文的金**老师,因为参加过县革委会大批判写作小组,而被“发配”到白云农场去劳动改造。同学们与金老师的关系特别好,大家去白云农场劳动时,也与金老师聊得很嗨,从不因为他犯了“错”,受了“处理”而产生一点点的生分感。特别是当年6月初的一个夜晚,根据上面的要求,由几位最高大壮实的学生骑学校的自行车把金老师接回教室批斗。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批斗老师”。但我没上去发言,因为金老师执教时,我编的“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手抄小报被金老师评为最佳,成为我中学时并不多见的高光时刻。但上讲台批斗的学生不是说废话,就是开玩笑,批斗会成了闹剧。班主任也不管,反正任务完成即可。批斗会结束,那几位男生又嘻嘻哈哈地送金老师返回白运农场。
那时候,我们家里确实穷(父母微薄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姐弟仨,还有山乡的奶奶)但父母虽不能让我们三姐弟吃好穿好,却能保证我们冻饿不着。加之住房是单位的,就医是免费的,上小学好像全免,中学交3元代管费。因此,上学九年,我几乎可说是无忧无虑。大概只有我出生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末年,也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因而姐弟仨就我有些先天营养不良。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的是,那时的食物虽然短缺,但绝对安全,从来不会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等。也几乎没什么食品添加剂。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饭菜真的特别香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食物少,抢着吃的缘故,而是食材确实环保新鲜无污染。没有任何的黑科技。
因年龄缘故,关于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笔者所知甚少。毕竟,那时笔者才刚入小学。大串联、大鸣大放、斗来斗去什么的,都没有啥印象。那时候的公审大会,安排在东阳中学大操场,我们到是经常要步行去参加,挨批斗被判刑者中,确实有一些是统称为“反革命”的人,至于他们具体反什么,反的对不对,我们很少会去思考分析。记忆中,那时候偷听敌台、写反动标语和贪污受贿是重罪。有个被枪毙的公社领导,就是因为收了他人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而遭刑。那时对乱搞男女关系也抓得很严,判的很重。那时的离婚率很低,根本就没有二奶小三之说。但生的孩子却比较多,有的人家生五个男孩,被戏称为“五雄狗”,很牛逼,令人生畏。笔者有时做梦都在想,我上面要是有三个哥哥多好。
那时的人们发型衣着都比较单一,有顶军帽有个军包有个军用水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让人无法移开视线”。但无论物质多匮乏,兜里多干净,人人看上去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男人女人除了雪花膏,好像就没什么化妆品了,更不要说什么美容店了,人人都具有朴素的健康之美,纯真又自然。
对我们中小学生来说,唯一能体现那个特殊时期特点的事,就是东抄西凑的大字报。我们学生的大字报并不是批斗某个人,其对象往往是苏修、美帝反动派、地富反坏右(集合概念)。自然也批过林彪和孔老二。当时,我们几乎人人都抄过“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样的句子。这类大字报自然是应景为主,而且主要是写在作文纸上作为语文作业完成的。
那时候最形式主义的一件事就是吃忆苦思甜饭了——各地有所不同,这里专指东阳人民医院食堂搞的——食堂师傅将玉米粉、米糠、米粉加一些素菜搅拌在一起,挺营养的,又加油盐多了点,结果变成了一道美食。大家吃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孩子们能聚在一起吃饭,可开心了。原本是“忆苦思甜”,却搞成了欢乐的节日。有个大孩子大声问道:“妈妈,你们以前的饭有怎么好吃吗?”大家听了忍俊不禁。
那时候能读的文艺作品确实不多,当年母亲给我买了一本现代革命京剧汇编,书里面有十个作品。其中《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中有很多对白或唱词,我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也是熟读成诵的。此外,自然就是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征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忆中好像这个是手抄本)等和电影文学剧本《地道战》《地雷战》《春苗》《决裂》《青松岭》《西沙儿女》(好像是诗体小说)《小兵张嘎》等。现在大家回头去看这些作品,你会发现她们思想之健康、语言之规范、情感之积极,恐怕是当今某些大咖作家都望尘莫及的。看这些作品长大的人,绝对不会去追求卖Y嫖C的享乐腐朽生活,不会去夸秦桧、李鸿章、胡适,更不会形成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崇洋媚外尤其是精日思想的。
以前,我们父母要教育我们三姐弟,还要三班倒工作,不觉得累;现在的家长只教一个孩子,而且还有老人搭手,却经常闹得鸡飞狗跳。为何?文化环境使然。在优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律精神远高于在庸俗病态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那时,父母几乎不用教导,孩子似乎坏不到哪里去,像我们的理想一是解放军,二是工人,三是小英雄。现在孩子的理想较复杂,文体明星、老板富翁、网络大咖、游戏高手当为他们的首选。当然,也有一些孩子(数量不多)以当科学家为荣。
那时候,我们年纪小,不太懂得领导的含义,也不会有什么敬畏感,尊重感。那时我们大院(三家单位合成)里有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市副县长),特别温和,没一点架子。他的夫人是上海人,有一子一女。儿子年龄与我相仿,但无论吵架还是摔跤,我及其他小伙伴们从不会相让。他的父母也不会因为儿子受欺侮了,便以官压人。我们的住房比他们还多一小间。唯一让我感到羡慕的,便是他们从上海回来,总会带一些奶糖。那个男孩,会拿一些奶糖来讨好大孩子,而与他年龄相仿且比他个子小的我,自然是享受不到的。每到这个时候,才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用今天的时髦语来表达,就是:羡慕嫉妒恨!
关于那场件持续了多年的事,当年的宣传和我们的想法自然是比较一致的。有首歌是这样唱的,“无产阶级*****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歌这样唱,文这样写,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当年,父亲有过一点小挫折,就是被单位里的一个坏蛋诬为小爬虫而被叫去陪斗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纠正。我们一家没挨斗,更没被殴打;反之,我们也从不斗人,更不殴打他人。故对特殊年代特定的事,在情感上确实说不出有什么厌恶感。当然,有极度痛恨的人,也有热情肯定的人。我算个中庸之道者。
但说实话,我亲身经历的十年,与诸多的回忆录和其他材料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伟人去世时,我们真诚的情感反应就和莫*、余*所描述的完全相反。这一点我不觉得他们一定在造假,就他们这个年龄来说,他们对伟人的厌恶甚至痛恨,或许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又或许是后来阅读反思的结果。
但笔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最近十年,笔者与同龄人及更年长的老人交流,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同情甚至肯定和憎恶甚至反对这个特殊年代里形成的这场特殊事件的人员,对党和国家的感情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有着十分奇怪的错位。这种错位,在各平台的文章及留言中得到显著的印证。但无论如何,这场认知冲突中,双方的思想观念差距甚大,基本相背。但他们都认为自己坚持的是对的,是在讲真话。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有感于此,笔者认为现在急需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鼓励63岁以上的老人(当年基本已懂事,能说出一点故事)作口述史。同时,可对每位老人的历史与当下的表现进行必要的审查,以判别其口述史的真伪。笔者认为 一个人的口述史说明不了问题,但成千上万个口述史,就能组成那个时代的历史画卷。这也是我作这篇口述史的原因之一。
来源:浙教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