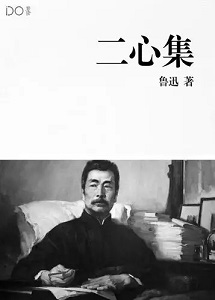穿过一望无际的稻田,公共汽车便沿着铁路线行驶,眼看就要进入繁华的市街了。
真理子把贪恋窗外景色的目光转了过来,对身旁的丈夫说:“快啦!第三站就是了。”
“真没想到,这个镇市还很漂亮哪。我原以为是更次一些的乡村呢!”
“你别趴门缝看人,把人瞧扁了。”真理子满面含笑,双眸凝视着自己的丈夫俊彦。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圆乎乎的脸象个小孩子,今天显得更加容光焕发。
大池俊彦和真理子是今年四月刚刚结婚的年轻夫妇。男的二十九岁,女的二十四岁。他俩在伊香保草草地结束了新婚旅行,为了补偿不足,现在利用秋假的几天空暇,到真理子的故乡——北方的N市来扫墓。俊彦一直生长在东京,对真理子所说的故乡,内心是非常憧憬的。还在结婚以前,俊彦就曾经说过:“到生你的故乡好好去看一看吧。”这里虽然叫做真理子的故乡,但是双亲早已去世,唯一的姐姐也把户口迁到东京,直系亲属一个也没有了。他俩寄宿在附近农村的伯父家里,扫完了墓,今天乘车来看真理子的故居。真理子和她的姐姐是在那里长大的。姐姐出嫁到东京去以后,真理子在读高中三年级的秋天,父亲死了。母亲等她高中毕业以后,变卖了房子,娘俩到了东京。母亲两年前也逝世了,真理子为了解除愁闷,参加了当地的文艺合唱团,结识了俊彦,并在当年春天与俊彦结了婚。俊彦是某电机制造厂的设计技师,真理子是一个商业公司的英文打字员,两口子都工作。他俩虽然结婚不到半年,但由于过去就有过一段交往,了解彼此的脾气秉性,所以感情十分融洽。
汽车到了邮局前面停下了。
“在这儿下车吧,过了那个拐角就到家了0”
真理子离开那里已有六年半了,可是说话的口气好象还住在那里似的。无论怎么说,她从出生到十八岁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只有那所房子和周围的街道才是她真正的故乡。
真理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下了汽车,俊彦提着手提包跟在后面。一走进拐角,眼前是一片古老的住宅地。当地由于多雪,家家户户的顶梁柱做得又粗又大,这在俊彦看来,是很稀奇的。
“不过,样子还是有些变化的。瞧!盖了很多的新房子啊!”
的确,在一些古旧房子的中间到处参差地建造了一些新的小住宅。样式和在东京周围看到的新建的出售住宅一个样,使人感到很不谐调。
真理子失望地嘟嚷着:“变成这个样子!不知道我住的房子是不是还在?!”
但是,不必担心。拐过纸烟店屋角,走了不到十米,她就快乐地喊起来: “在那哪,那个二层楼。嘿!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呀!”
那是一座古老的房子,周围是混凝土的墙,从哪个方面看也不出奇。可是,真理子抬头仰望,回忆起往事,两眼不由得被泪水模糊了。
“瞧!二楼的右边有个窗户吧?那是干燥室。再远一点的那间房子是我读书的地方,左边的里问是大学生八木先生寄宿的房间。它的楼下是饭厅,母亲经常在那里干活,熨衣服。”
“啊,我们要能到里边看看该多好啊!我想,如果说明理由,一定会让我们看的。”俊彦温和地说。
真理子摇了摇头说:“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外边看看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房子,也算达到目的了。”
房子的内部,因居住的人不同而变了样,恐怕看了的话,只会使人失望。楼里,原来真理子和双亲居住的房子,现在变成了干燥室,里面晾着小孩裤子和背小孩用的花带子,看来住户好象是一个有小孩的家庭。门旁还放着一辆小孩车。这些都和过去不一样。尽管这样,还是来看看好。因为从外边看,几乎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就连庭院里的木门也是过去的样子,令人觉得当年手拿铁锹的父亲,现在好象又出现在那里。
这座房子对真理子来说,看也看不够,想也想不完,但对丈夫来说,可能是无聊得很吧。想到这里,真理子说:“啊,我们再去看看我小时上过学的学校吧,已经离这很近了呀。”
坚强而又多情善感的俊彦,并不象真理子担心的那样寂寞无聊。他想象丰富,精神愉快,说:“好,头前带路。你呀,那时候还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哪!我妤象看到了你当年穿着海军服,上学迟到了,就从这个门匆匆地跑了出去。”
“这边,就是往学校去的道路——小学和中学就在对面啊。”
正准备走,真理子忽然看到了邻居的门牌。那是她家左邻的房子,也是二层楼,混凝土墙,门柱上挂着“山中”的门牌。
“邻居也变了哇!原来住在这里的是田津野大叔,不晓得房妮现在怎么样了?”
“房妮,是这家的孩子吗?你的好朋友吧。”
“一点也不错,是好朋友。她和我同岁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
田津野房代是个心理发育低下的孩子。脸儿白净净的,很标致。有一双美丽而灵活的大眼睛。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智力迟钝的样子。
“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正因为那样,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
真理子一边同俊彦并肩地走着,一边吃吃地笑着,开始讲起了故事。
那是真理子刚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一个星期日的早上,真理子听到门口邮箱有放入邮件的声音,便拖拉着凉鞋走出去了。她刚取出信件,就传来了巴嗒巴嗒的脚步声,原来邻居的女孩也警觉地跑出门来。
真理子满脸堆笑地打招呼: “房妮!”
房代小的时候得过麻疹,因为发高烧转成脑炎,直到现在,智力还象四、五岁的小孩一样。真理子和她同学到小学三年级,以后她没有继续求学,一直在家里病病歪歪的。可是,在房代幼小的心灵里,始终记忆着过去和真理子一起玩耍、手拉手上学的情景。不知不觉地两个人成了亲密的伙伴,就是不上学了,房代也还把真理子当作朋友。
过去上学的时候,房代常说:“巧(小)真理,还有卓(作)业哪,可我没精神做了,这不好啊,再加一把劲,就可以整整齐齐地做完了。”
房代有些咬舌头,说话稍一紧张,就流口水。她学习很吃力,对字母和简单的汉字好不容易才能念出声、写下来。在笔记本上并排写了好多自己的名字。但是作业还是能够耐心地去做。每当这时,真理子总象哄小孩似的大加夸奖,并惊异地看着她。真理子从少女多情善感的心情出发,认为“对可怜的孩子一定要关心”,所以对她象盆火似的,非常热情,非常亲切。
真理子偷偷地向邻居的门里看,正好房代从邮箱里取出二、三封信。房代的身量和真理子不差上下,但比瘦纤的真理子长得丰满、娇艳。
房代一看见真理子就诉苦地说: “杏(信)还没来哪。”
“信不是来了吗?瞧,三封哪!”
真理子说完,房代闷闷不乐地说; “没来呀,又一回没来啦。”
房代珠泪滚滚。三封信,都是给她父亲的。她多少能识一些字,看到没有自己的信,就悲伤起来。
“不要哭哇,给房妮的信过几天就会来的。”
真理子信口地安慰着她。
“真的?能来?”
“会来的,早早晚晚。”
“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
房代兴奋地问道,真理子有些发窘了。
“啊,明堂(天)来吗?嗯?”
真理子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
“说不定明天还是后天,反正一定能来呀!房妮。”
“真叫人高景(兴),杏(信)来了,接着,杏(信)又来了。”
房代快乐得转圈儿跳。真理子急忙向自己家门跑去。可是,当她刚要跑进门的时候,撞上一个站着的人。她慌忙地停下脚步一看,原来是大学生八木和道。八木为了在市内大学走读,通过真理子父亲的上司关系,从去年开始寄宿在真理子家的二楼。他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好象不那么好,然而五官却长得端正,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对人的态度也和气。真理子站在他的面前,对于平时没那么注意的自己的微黑的皮肤、瘦小的身躯,不由得感到惭愧起来。倒不是说她,爱上了小伙子。可她是个小姑娘嘛,对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怎么能毫不介意呢!
“真理小姐,美滋滋的哪,心里想着好事吧?”
八木好象看见了真理子与房代的交谈情况,露出了什么都明白了的表情,微笑着点点头。
“烦你!八木先生,那么,你说是什么事?”真理子脸红了。
“用不着瞒我。你呀,想给邻居那个小女孩写信,对吧?了不起!”
“你瞎扯!什么了不起!……”
真理子跑进自己的家,上了二楼的学习室。她高兴极了。因为自己的想法不仅可以使别人称心如意,而且得到了八木的夸奖,简直乐得有点坐不稳站不安了。她从抽屉里拿出带花的信纸开始写信了。
房妮:
你好吗?春天到了,天气暖和了,多好啊!房妮,你天天坚持打扫院子,真令人钦佩啊!
再见
真理子写完时再三考虑:怎么办呢,写不写自己的名字呢?最后还是决定不写了。做好事只有谁也不知是谁做的,心里才高尚哪。她用一个单色的信封,写上收信人的姓名,贴上了邮票。真理子一边手里拿着信,一边哼着歌子,下楼走了出去。
第二天,真理子从学校一回来,就看见房代在她家的门旁蹑手蹑脚地走。她看见真理子,马上跑过来,高声喊道:“杏(信)来啦,瞧,又来啦。”
房代过于兴奋了,下巴上流满口水。她手中拿着的带花的信封,已经揉得满是皱纹。
真理子每周都给房代写一、两封信。在发信的第二天偷偷地向房代家里望着,心里美滋滋的。有一天,她从房代母亲那里听到了感谢的话。信上虽然没有署名,但是,房代母亲知道,给房代写信的,大概除了真理子没有别人。她说:“那孩子,高兴的哟,把信都当成了宝贝,收在匣子里,连我都不让碰呀。”
稍停了一会,房代母亲又拜托说:“在信上是不是可以写上: ‘每天早晨要规规矩矩地刷牙?’或者,请写上‘吃饭时不要贪玩儿’。”
房代对信上所写的事,简直象圣旨一般,认真地去傲。房代的母亲送来了邮票和逗人喜欢的带画的信封,再三说: “光是写信,就不知道该多么感谢了。”真理子一听,更加得意了。她的双亲,看到女儿做好事荣获致谢,心里也很愉快。以后,真理子就把房代母亲的嘱托适当地编进信里,陆续地寄出去。“可不是,你做的是一件漂亮的事情啊!”俊彦打趣地说,但脸上却露出了钦佩的表情。
“那么,那信继续到什么时候?到了东京以后还寄过吗?”
“原来想寄出好多封,但是,不知不觉地就停止了,因为还有比这更迫切的事要做!”
真理子上高中的那年秋天,父亲因患脑出血突然去世了。第二年春天,母亲和真理子把房子卖掉上东京。寄宿的八木,搬到了附近山货店的二楼。当时,真理子心中充满着惜别之情。
在东京落脚以后,母女二人住在离姐姐家不太远的公寓里,天天出去上班。真理子在一家商业公司——不是现在的公司——就职,夜间到打字学校走读。那时,生疏的生活环境弄得她精神很紧张,每天为本身工作而疲予奔命。
真理子这次回到故乡,几乎没有想起房代的事,也没敢想和房妮重逢的快乐。在瞬息万变的今天,六年的时光,是那样的漫长啊!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探望了,不能连房代也不想会见啊。但不知她搬到哪里去了。”
二人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小学校的前面,正好赶上休息时间。在校园里,穿着各式各样海军服的孩子们,叽叽哇哇地吵闹着,象一群高声欢叫的小鸡崽。
“唉呀,校舍变成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了,可是,那个角落的老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啊!”真理子睁大眼睛望着。
中学的校门位于小学校的斜对门儿,这也是真理子的母校。在中学墙壁的尽头有一间文具店。店门前,一个年轻的主妇正在哄着怀抱中的婴儿。
“啊,梅井,那不是梅井姐吗?”
真理子满怀深情地喊着跑过去。
“哟!佐藤妹子!”那个年轻的主妇走出了店门。她所说的佐藤,是真理予的娘家姓。
梅井茂子是真理子中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嫁给这个商店老板的大儿子了。真理子一面向梅井茂子介绍自己的丈夫俊彦,一面打听往日同学的消息,然后问道:
“啊,梅井姐,你知道我的邻居房妮吗?她,不知搬到哪儿去了。”
当茂子听到这话的时候,立刻收起了笑容,脸色一下子变了。
“啊,房代她呀,被人杀害了。”
“被人杀害了?”真理子大吃一惊,“什么时候被杀的?”
“你搬到东京去的时候。那年的六月也许是七月,我们这儿非常乱,有一天夜间房代被杀死在杂树林里,凶手至今下落不明。”
房代虽说是已经十八岁了,但还和小孩一样。象她那样的人,谁也搞不清楚,怎么会在夜间到那样的树林中去呢。房代死后,她的父母怕看见老房子想起女儿,就搬到车站对面去了。真理子听了这些,怎么也不能相信。
梅井接着说:“那个时候,我们这儿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乱子。房代被杀的前几天,强盗抢了瑞光堂。”
梅井所说的瑞光堂,是这个城市唯一最大的营业——贵重金属专卖商店。那天,三个强盗闯进去,把店主夫妇绑起来,抢了宝石逃跑了,至今罪犯仍逍遥法外……
真理子打断她的话说:“真没想到,房妮竟遭到了那样的不幸……若是真的,我想去给她烧炷香,但不知她父母亲现在住在哪里。”
“打听一下站前的那个印刷厂就知道了,那里的女主人是田津野大婶的远亲。”
那里是市街的热闹地方,打听到房代父母搬去的地方是不成问题的。
真理子向俊彦道歉说:“真对不起,拉着你到处转,去的都是与你八杆子打不着的地方。”
真理子话音刚落,俊彦就说:“没什么,也许前世有缘吧!我也给她烧上一炷香!”
房代的双亲住的房子比原来的小,但很舒适。也许因为只有老俩口住的原故吧!房代的父亲出去上班了,仅母亲一个人在家。
“唉呀,真理妮!”
房代的母亲一看见真理子,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了起来。她过去的面容和自己女儿栩似,白嫩而丰满。可是现在差不多已经于瘪了,变成了一个小老太婆。等他俩在漂亮的佛坛前给房代烧完了香,房代的母亲立即拿来了菜汤和点心,不觉时间已过晌午了。
“说起那件事,我们老俩口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真理妮还记得吧,那个孩子腼腆得很,一看到生人就害怕,一个人从来没有走远过。怎么也没想到她在夜间那么晚出门了,而且一直走到河对面的杂树林里。我想,多半是她在院里的时候,被谁强行领走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被拐骗走了。如果是那样,她为什么不大声对我们喊呢?那时,我也好,她爸爸也好,都正在二楼呀。”
事情发生在七月二十二日夜里,那时房代的父亲正迎着夏天的晚风坐在二楼乘凉,母亲整理着他的衣履等什物。晚上九点钟,房代的父母才发现房代不在家里,他们非常担心,立刻到附近去寻找,但怎么也找不到,到了晚上十一点半,从警察那里得到了通知,说是在杂树林里发现了一具被扼杀的女尸。发现的人,是个中年男工人,他因为有事回来晚了,想在树林里抄个近道,可是突然发现一个年轻姑娘靠在懈树根旁死了,吓得他马上跑到附近的警察派出所去报告。据分析,房代是被男人的大手卡住脖子勒死的。除此以外,没有别处受伤。断气的时候大约是在九点半左右。从房代家到杂树林的道路,是一条只经过河边和旱田的荒凉小路,几乎很少有人走,所以没有找到目击者。但是,如果作案不在人少的地方,到处都有人家,一个将近二十岁的姑娘,一边哭喊着一边被人拉着走,就要引起人们的怀疑,一定会有人报案的。
“过去真理妮真是给了很多帮助啊。——到了东京以后,还一直收到你的信哪。你寄来的画有东京塔的明信片,房代高兴得什么似的,可是……”
房代死的时候,她家给在东京的真理子也发了通知,但真理子没有收到。那时正好赶上真理子和她母亲搬了家,以前公寓的管理员是个吊儿啷哨的人,也许把邮件弄丢了。
房代的母亲双目低垂,对俊彦说: “真理子写来的信,那个孩子都保存在匣子里,象心肝宝贝似的,非常爱惜,非常珍贵啊。在我跟前除了房代,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经独立生活了。我们老俩口一想到我们死去以后,房代一辈子都要给哥哥和姐姐增加累赘,觉得她早点死了也好。不过,如果是病死,那就没的可说了。谁知死的是那样的惨啊!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抓到那个千刀万剐的凶手,可是……”
看到房代母亲的样子,两个人心中非常难过,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田津野家。俊彦姑且不论,可对真理子来说,却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打击。故乡秋天的明朗天空,好象突然变黑了。原来她曾作过一个愉快的计划,就是看一看故乡的亲友以后,陪着丈夫参观一下过去游览过的名胜古迹,可现在完全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心情了。她一方面心里觉得对不起眼前并排走着的丈夫,一方面心情沉闷,默默无言,不知该怎么办。
俊彦有意地安慰着自己的妻子,说: “找个幽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吧!这一带有风景优美的地方吗?”
“风景优美的地方啊——可是,我认为没有象东京塔那样优美的地方,……”真理子刚想说,突然又闭上了嘴。
“你怎么啦?”
“啊,我发觉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田津野大婶刚才说的:‘房代非常喜欢绘有东京塔的明信片’。”
“那是怎么回事? ”
“奇怪呀,我不记得给房代寄过什么东京塔的明信片啊。”
“不记得寄出过吗?可是那位大婶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
“可是我寄给房代的一直是信啊,的确一回也没有用过绘画明信片呀。我从来也没有使用明信片的习惯。”
“真奇怪啊。”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
“喂,再到田津野大婶那儿去一趟,行吗?我想对证一下。”
“我也认为这样做比较好。”
两个人又从原路回去了。房代的母亲,一看到他们二人又回来了,好象有点惊讶,说:“是啊,确实有画着东京塔的明信片呀,不信我拿出来你看!”
“啊?信还收着吗?”
“全都收着哪。那孩子生前是那样的爱惜它,本应埋葬的时候一块入土才好。可是那件事发生的那样突然,好象晴天打了个霹雷,我一下子变成了病人,顾不上考虑那样做了。再说,看到那些东西,就叫我想起那个孩子,使人心酸,那样处理了也舍不得,所以都原封不动地收藏着。”
房代的母亲站起来走进里屋。不一会儿,拿来两个硬纸做的旧糕点匣子。
“匣子还是那时的原样。那孩子把信放到匣子里谁也不让动,我也没有仔细看过。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一发现自己放的东西的样子哪怕有一点变样,立刻就知道,并且大哭大闹。不过,的确是寄来过画着东京塔的明信片,我想也一定放在这匣子里面了。”
真理子接过匣子急不可待地取下了盖子。
“这么多呀。”
俊彦发出了感叹声。但真理子胸口好象堵住什么似的没有吭声。匣中的信封,有画花方块的,有画着天使漫画的,有画着小猫的,……无论是哪一种都非常眼熟。信封上都用钢笔写着收信人田津野房代,字迹秀丽,一眼就看出是姑娘写的。两匣信合起来大概有五十多封吧。每当来了一封信,房代总是打开看,看完装到信封里,又拿出来看,象这样的事不知反复几十次,一直到下封信来了为止。那些封信都被弄得皱皱巴巴,纸角都磨破了。真理子好象看见房代两眼发光,流着口水,把信装进去又拿出来的样子,心中非常难过。
“喂,东京塔的明信片,在那儿!”俊彦指着信封中间夹着的露出一半的绘画明信片说。
“啊,这,这不是我写的字呀!”
真理子马上把明信片翻过来大声喊着。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字体很拙劣。信上写道:
房代小姐,你好吗?这是东京塔。房代小姐,过几天请到东京来玩吧。祝健康。
再见
“不对呀。我从来不写房代小姐,而且给房妮的信一定用拚音字母写啊!”
“邮戳是怎么盖的?”俊彦问。
“盖的是N市,装作好象是从东京发出来的——”
真理子开始在信堆里乱翻。
“还有带画的明信片吗?”
“带画的明信片只有一张啊。可是——”
真理子找了一会儿,不久,顺手把三封信拿出来放在席子上说。 “这三封信都不是我写的,信封的样式也没见过哇!”
三封信中有两封信的信皮上画着白雪公主和小人。信封上的字也是圆珠笔写的,字迹和刚才看到的绘画明信片上的字同样拙劣。另一封是用钢笔写的,画着向日葵花。
俊彦从一旁伸出手,按住一封画有白雪公主的信说:“喂,真理子,这个信封上的邮戳是——”
“这是——昭和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两个人的目光不觉碰到一起。这个日期不正是房代被杀的前一天吗。真理子急忙从信封中抽出信来看。信上写道:
房代小姐,今晚九时,请到树林里的地藏王菩萨庙来。因为要给你好东西,请一定来呀。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来吧。
再见
“这是……”
真理子自己都觉得脸色变了,在旁边看信的俊彦也是一样。
“谁把这样的信……那孩子就是因为这封信……”房代的母亲把身子向二人前挪了挪,难以忍受地喊起来。
很明显,房代就是被这封信引诱出去的。信上说的“今天晚上”,指的是二十二日晚上,写信人是经过认真计算的。因为发信时间是二十一日,第二天房代才能收到,当晚九时就可以到树林里去了。
“把另外的信也打开看看吧,快点。”
没等俊彦把话说完,真理子又拿起一封画有白雪公主的信,邮戳上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信上写道:
房代小姐,你好吗?今天你如果打扫院子,扫完了,请把扫帚和簸箕放在门外边。一定要把扫帚和簸箕放在外边。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俊彦停了一会说:“这是一个考验。”
“考验?”
“这个凶手了解到,房代把信中的指示当作神意一般接受和服从,可是,是不是真的那样,还缺乏自信。所以,发出了扫完院子以后把扫帚和簸箕放在门外的命令来试一试。我想,房妮大概是遵命了。于是,有了自信心的凶手,接着就发出了这样的信:到树林中地藏王菩萨庙来。”
是的,这个分析是不错的,真理子也是这样想。房代忠实地服从真理子在信中叫她做的事情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不知是那个家伙利用了房代的天真无邪,夺去了她的生命?
真理子最后打开画有向日葵的信封,信纸的花样和信封一样。字不是用圆珠笔而是用钢笔写的,写得不算好,但是比起画有白雪公主的信要写得工整。日期写的是七月十八日。信上写道:
房妮,房妮是很聪明的呀。请把这个绿色的小袋子小心地收藏起来。对谁也不要说,谁也别让看,好好地收藏起来啊。一直收藏到我下一次给你写信的时候,叫你把“绿色的袋子拿来”的时候为止。在这期间一定不许丢了。
再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所谓绿色的袋子是什么呢?向信封里看了看,没有发现;检查了另外一些信,也没有找到哪里夹有绿色的袋子。
俊彦向房代的母亲打听:“房代是不是认为这些信的发信人都是真理子,或者压根儿就没想过发信人是谁?”
“我想,她大概没有考虑过谁发的信。每当接到信都非常高兴,好象不知道是真理子给寄来的。对那个孩子来说,来信就好象自然而然吹来的风一样啊。我们从来也没有告诉过她,信是有发信人的。因为她如果知道是真理子给写的信,就会死乞白赖地要求再写吧,再写吧,也会要求回信什么的,这就更麻烦了。——只因为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如果这样想的话,就会废寝忘食地想这件事。”房代母亲可怜地微笑着。
“可不是嘛,那么,真理子到了东京以后来信不太多了,她不感到悲伤吗?”
“好象多少感到一些凄凉,可是不太严重。我也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真理子的负担,所以常挑好听的话对她说:‘因为房代已经长大了,别人来的信就渐渐少了。可是,只有带画的明信片和信寄来的时候,房代是非常高兴的,但是……’”
房代的母亲和俊彦说话的时候,真理予把三封信和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并排地放在膝前思考着,突然她的眼睛亮了。
“啊,请看一下,这张绘画明信片上的东京的‘京’字”。
俊彦把绘画明信片接在手里。
“嗯?错了,笔划多了一横儿啊。”
东京的“京”字多了一横,大概是同“东”字中间的日字混同了。仔细一看,同样的错误重复了两次。
“我,我知道一个人习惯于把‘京’字中间的‘口’字写成‘日’。想起来了,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那个少年是他们班里的劣等生。国语老师经常笑着说:
“象老弟这样写, ‘京’字,真可以说是‘过犹不及’啊。不过,无独有偶,明治年间好象也有把‘京’字中的‘口’写成日字的人啊。”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把写“京”字多加一横的毛病去掉。
“那个学生住在什么地方,离这近吗?”
“啊,他住的地方离刚才看的我家房子只隔五、六幢。”
因为房代的母亲对真理子的好意,非常高兴,对附近的人也常讲。住在附近的人,知道真理子给房代写信的事,并不为怪。
“告诉我,真理妮,你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马上去报告警察。”房代的母亲麻俐地站了起来。
“可是——”
真理子踌躇了。她感到就这样控告一个人为杀人凶手,证据是不足的。俊彦了解她的苦衷,站起来说:
“捉贼要拿赃,我们再加把劲调查一下吧。大婶您不要过于着急啊,请稍稍等一等。”
在中学校邻近的文具店里,今天早晨代替茂子看铺子的好象是她的丈夫,大约三十岁左右。真理子从皮包里拿出借来的三封信。
“你知道不知道,贵店出售过这样的信封吗?”
店主人把信封拿在手里,看了看说:
“向日葵的啊!怎么?不记得卖过啊!不过,这里卖过的倒和你另外的两个信封是一样的。”
“啊,是白雪公主的吗?”
“是这个,我记得我们店卖过。大约是六年以前,我接店的时候卖过,查一下帐簿就清楚了。”
“六年以前啊,这信封卖给过一个男人吗?”
“卖给一个男人?把白雪公主? ”这时正好他的妻子茂子,提着菜篮子回来了。看见真理子他们又回来了,好象有一点出乎意外。尽管如此,她还是和蔼地笑着。
“卖给一个男人?——是呀,如果是家母卖的,也许还会记得。因为,她老人家的记性很好——喂,茂子。”
店主人把信封交给了妻子,叫她去打听一下。茂子拿着信封走到里屋去了。不一会,就回来了,说。
“母亲说想起来了——那个人啊,原来是我和佐藤妹子过去的同班同学,姓松代。母亲说,要是女的来买就不能一个个记得了。可是身材粗大的男人买那么漂亮的信封,觉得可笑,还开了他个玩笑哪!所以记得。”
“松代,不错——”
真理子叫起来。过去把东京的“京”字写错的同学正是叫松代贞夫。
一走出文具店,俊彦小声问: “真理子,怎么办?”
“我去见见松代。”真理子用坚决的口气说。
刚才从茂子那儿打听到,松代在运输店当司机,从这里到他那儿只需走五分钟。
“但是,仅仅抓住这一点证据,就去报告警察,那不行吧?”
“是的。说不定,他也许会是滚刀肉,要百般抵赖。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有点棘手了。不过,我呀,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使凶手老老实实地招认。不那样的话,我对不起房妮——因为房妮是那样喜欢我给她的信,不论什么事情都照着办啊!那是……”真理子的声音有些颤抖。
“明白啦!我来设法帮助你,一定要实现你的心愿。”
两个人快步地走了出去。
运输店的门口大约只有一间半房,是个小店。但后面的停车场相当宽阔,职工的宿舍是二层楼,看来买卖做的挺大。
店里,一个中年男子正在打电话。他放下话筒,扬着脸,粗声粗气地对真理子他俩说:
“松代啊,现在出外办事去了,我想不久就会回来的。”
两个人决定在店前等待。在洒满秋天阳光的柏油马路上,老奶奶背着小孙子摇摇晃晃地走着,小孩子兴高采烈地追狗玩。真理子虽然站在明亮而温暖的太阳光下,但是身体不自觉地轻微地颤抖着。她心里充满着紧张和恐怖,加上无法抑制的愤怒。她想:当房代发现信件辜服了自己的信任,而被一个陌生男子勒住脖子的一瞬间,该是怎么样的恐怖啊。尽管房代怎么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要那样会面,但她对真理子毫无抱怨。
从道路的右边开来的一辆中型载重汽车,减慢了速度,停在运输店的前面。
“是他呀。”真理子的表情严肃起来,小声地说。
穿着茶色工作服上衣的驾驶员从驾驶室的右门走出来,一个似乎助手的少年从左门走出来,穿茶色工作服上衣的就是松代贞夫。他虽然带着深色的有色眼镜,但一看他的下巴就认得出他来。
“是松代!”俊彦靠近真理子小声地说。
松代把有色眼镜推到眼睛上面,惊讶地转过身来。但是,一看见旁边站着的真理子,两眼吓得发直了。
“想起来了吗?我是佐藤真理子,这是我丈夫。”
松代默默无言,虽然好久没有见面了,但没有一点怀念之情,就象半路上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彼此都很无所谓。
“松代君,找你有一点事情。关于田津野房代的事。”
松代听到这句话,吓得脸色发白,脸形都变歪了,用嘶哑的声音说:“你,是特务警察吗?”
“不是,我们拿到了证据,就是你给房代的信。”
“错了,错了,不是俺,干掉她的不是俺。”
松代的脸充满了恐怖,使劲地晃着脖子。
“噢?别的不谈,是不是先找个什么地方谈谈问题。不过,请你记住,如果逃跑的话,对你会更加不利。”俊彦严厉地再三重复说。
松代向离他很远站着的摸不着头脑的助手说:“喂,俺,有点不舒服,想休息一下,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说完,就出人意料地急速走了。
离这二、三十米远的空地角落里,堆摞着一些陶土管子。
俊彦面向那块空地喊了一声:“跑!”三个人并排地跑起来。
“我说的是真的,干掉那个孩子的不是我。”
松代激烈地摇着头,汗水落在膝盖上发出了声音。
“照你这么说,把这个寄出去的莫非不是你吗?”
俊彦让他看了看手中的信封,松代哑口无言。
“说的不对吗?”
“是俺,寄信的是俺。”
“你写信,是想把房代引诱到外边去,对吧?”
“是的。”
松代挣扎着,用工作服的袖子擦着脸。
“象我这样的,象我这样的啊,学习不好,脸子长的又丑,女孩子谁也看不上,找对象很困难。房代那姑娘,脑子虽然有点糊涂,但长的漂亮,身体也结实。所以——”
“所以,是不是想叫出来调戏她?”
“嗯,是的。我过去就听说过佐藤经常给她写信,她把信收起来,谁也不让看。有一次,她母亲来找家母缝东西,详细地说过这件事。于是,我就想出个主意,寄出一张明信片试试看。那张明信片是我过去去东京时买的绘画明信片。以后,我就在信上告诉她,把什么扫帚啦等等小东西拿到外边去,结果她照样做了。由于她完全照着信上说的做,所以,我在信上就写上了到地藏王菩萨庙来吧。”
“那么,你去了吗?”
松代耷拉着脑袋点了点头。
“我去的稍早一点,躲在树荫里等着,森林里漆黑一片。我想,她这个人糊涂,就是会面以后也不会向别人讲谁在这里找过她。至于想杀她什么的,完全没有想到。我说的是真话——等了一会儿没来,我想,也许信被她父母看到,突然不来了。我又想,即使信被发现了,也不会被人知道写信的是我——可是,正当我在草丛里要蹲下去的时候,传来了脚步声,确实是那个姑娘来了,还唱着什么歌,因为快靠近了,我正要站起来,突然跑过来一个人,那姑娘发出了悲哀的喊叫声。接着一阵劈里拍拉的厮打,最后好象有什么东西倒下去了,不久安静下来。我非常害怕,吓得连气都不敢出——我发现他确实是个男的——他向对面走去以后,我还目不转睛地盯了他一会儿,然后悄悄地回家了。因为害怕,我从房代身边走过时连看都没敢看。至于房代被勒脖子杀死的消息,是第二天以后才昕到的。我说的一点假话也没有。”
松代的语调很严肃,不能认为是信口开河。“松代君,刚才你说‘房妮发出了悲哀的喊叫声’,那仅仅是悲哀的喊叫声,没有说什么吗?”真理子问。
不管是什么样的小事,只要能提供线索,她就都想弄清楚,并把它收集掌握起来。
“那个呀,我以后也反复想过,可是都没有弄明白。我记得她好象说‘放开我,咩咩!不行,咩咩!’我怎么也弄不清那是怎么回事。”
“咩咩先生?”真理子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H市某建设公司工作的八木和道,接受了警察的审讯,终于供认了罪行。他就是以前曾在真理子家寄宿的那个学生。
在六年前的初夏,他和另外两个同伙,闯入了瑞光堂贵重金属商店,抢走了十多个宝石,当了强盗。三个人均分了赃物以后,其中两个人,各自离开了本地。因为他们一个是没有固定住处,行为不端的家伙;一个是出售荞麦面条铺的伙计,所以能很简单地搬到外地去。而大学生八木,搬走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在山货铺里过着寄宿的生活。
可是,当他探听到警察要到附近来的消息时,变得不安起来一一其实,这和瑞光堂事件没有关系,而是收查贼窟一一他因为赃物在手,非常害怕。
他过去,一直住在真理子家,完全知道真理子给房代写信的事,就打算利用一下。他用手头现成的绿色碎布片缝了一个小袋子,把宝石和信一起装进少女用的有向日葵花样的信封里,寄给了房代。
房代果然象希望的那样,把那个小袋子珍贵地保存着,谁也不让知道。可是,当房代意外地从松代那里收到诱惑信的时候,事情就朝着预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因为房代把松代的命令:“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来吧”,误解为“拿着绿色的小袋子,来吧。”
她紧紧地接着绿色的小袋子急急忙忙地向树林中走去。途中碰上了外出回来的八木。如果是以前,他对房代是从来不理睬的。可是,这个时候,当然要加以注意了。他用手电筒向她照着。只见房代一边鼻子里哼哼着歌曲,一边快步地走着,手里还紧攥着绿色的小袋子,这时,他吓得心都快跳出嗓子了。他立刻在房代的后边追赶着,想在林中夺下袋子。但因为房代大声喊起来,他怕让过路人听到就糟了,于是就不加思索地把她勒死了。
在结案后的第二天,真理子和俊彦坐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真理子望着车窗外闪过的一片片金黄色的稻浪,心中充满了悲哀。
“还是忘记了吧,”俊彦把胳膊放在真理子的肩上说:“你纯粹是一片好心,可恨的是那些混水摸鱼的家伙。”
真理子点了点头,但内心终是难以忘怀。不过,为了俊彦的原故,也要使心情开朗起来。
“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就是房代女士管那个犯人叫‘咩咩’这是什么意思?”俊彦询问道。
“因为那个人姓‘八木’(注:日语“八木,和“山羊”发音一样)。我和房妮住邻居的时候,房代曾打听过‘他姓什么’。我告诉她是‘八木’,房代听了就高兴地喊‘咩咩八木’。”作案的树林里,虽然黑暗,房代的感觉即使不如我们那样锐敏,什么嗅觉啦、第六感啦都有些迟钝,但仍然知道袭击她的是八木。咩咩是房代给他起的外号。我告诉她‘八木听了会生气的’不要当面叫。可是八木走过的时候,她还是一缩脖就叫: ‘啊,咩咩先生’这是只有我们俩才懂得的私房秘话。”
真理子说完,凄然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