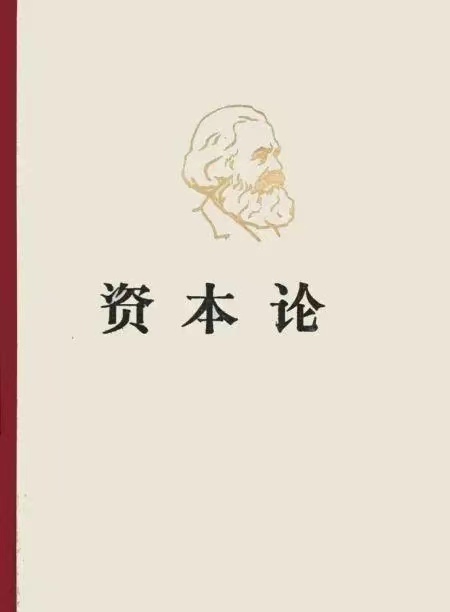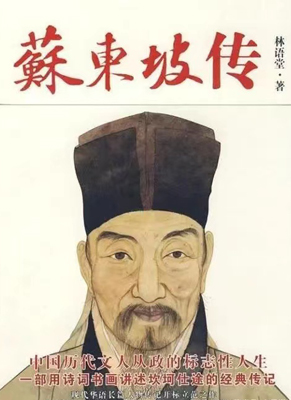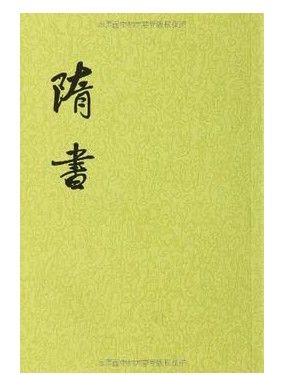1月29日,毛泽东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道:
“欢迎进步。”
1月间,毛泽东指示卫生部派出医护小组赴瑞士,迎接身患癌症的斯诺来到中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以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
斯诺是在1971年2月离开中国后返回了瑞士。是年冬,经医生检查,他患了胰腺癌,癌细胞已经多处转移,手术后病情日益加重。毛泽东得知后,指示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多次前去探望和慰问斯诺。
此次卫生部派出的医护小组由马海德、黄国俊、李钟萍、徐尔难组成,他们来到斯诺家里,发现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斯诺在保安为毛泽东拍的那张。斯诺对毛泽东的深情,使医护小组的大夫们极为感动。
马海德向斯诺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邀请。斯诺沉思了好久,才慢慢说道:
“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情,他们对于我在当前的困境中,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激。我知道在中国,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对此我深深感激。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
过了一会儿,斯诺慢慢地摇摇头,说:
“但是,你知道,我是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添累赘……”
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情况,周恩来指示医护小组就地为斯诺治疗,又从阿尔巴尼亚中国医疗队抽调了两位医生和4位护士到瑞士,组成了一个家庭小医院。经过几天治疗,斯诺的病情终于有所好转了。
1972年2月5日,周恩来将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于1月22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批示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进口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成套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
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专程到瑞士探望斯诺,转达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亲切慰问。当马海德陪同黄华来到斯诺的病床前时,斯诺显得很高兴,握住他俩的手说:
“3个‘赤匪’又见面了。”
2月12日凌晨,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直摆脱不了病魔折磨的毛泽东,由于患有肺心病,在心律失常、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她发现毛泽东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他也没有反应,就立刻大声喊人。
张玉凤回忆说:“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此时已成为毛泽东的卧室和治疗室——笔者注)。”
吴旭君对张玉凤说,快请医生!医生们闻讯,不敢怠慢,飞也似地赶了过来。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原因,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经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
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他扶起毛泽东,用力并有节奏地捶着毛泽东的背部,还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张玉凤也在一旁叫着:“主席,主席……”
此时,周恩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飞驰赶到毛泽东的住所。他由于过度紧张,下车时,许久迈不开腿,下不了车。如果毛泽东抢救不过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周恩来是清楚的。他动情地说:
“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据跟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着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的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20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了,他慢慢地睁开双眼,看到眼前的一切,有些愕然,平静地说道:
“我好像睡了一觉!”
经过这场大病,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的人小心翼翼地尽量不使他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会对他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有时需要热毛巾,或者需要换垫子,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
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39度5,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就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又风趣地说:
“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了,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2月15日,斯诺在瑞士逝世。在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斯诺在没有痛苦的昏睡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留下的遗言是:“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
2月16日,毛泽东给斯诺夫人发去唁电,唁电中写道:
斯诺夫人: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 2月16日
后来斯诺夫人根据斯诺生前的遗嘱,在1973年10月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毛泽东献了花圈。
再说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指示北京机场在停机坪两侧矗立两块巨大的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周恩来到机场检查工作时,见到立有这样内容的大标语,怒气冲冲地质问机场负责人:
“尼克松总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你们怎么能搞这样的标语?”
机场负责人告诉周恩来:
“这不是我们自作主张,是毛主席让挂的。”
于是,周恩来便去问毛泽东,说:
“我刚从机场回来,见到两副标语,他们说,是你让挂的。”
毛泽东说:
“你的意思呢?”
周恩来说:
“我看不好吧,人家毕竟是第一次来嘛,总该给人家留点面子嘛!”
毛泽东说:
“你给他面子,他能给你面子吗?第一次你要软弱不敢出手,他第二次就敢欺负你,接下来他就敢骑在你的头上,拉屎撒尿。”
周恩来说:
“那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挂?”
毛泽东说:
“对!第一次就要给他来个下马威!这叫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此前,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曾受到了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也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听了这些消息,他说:
“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2月21日这一天,北京是一个寒冷的日子。
毛泽东在尼克松的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前,突然提出:今天就要会晤尼克松。他叫身边的人给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
“请总统在午饭后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会见他。”
此前,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间还没有定,这一下可忙坏了工作人员,他们有的赶紧整理会客厅和卧室,有的给毛泽东剪发剃须,准备服装。
上午11点27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空旷、宽阔的北京机场徐徐降落。北京机场停机坪的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11点30分,尼克松面带微笑跨出机舱,和夫人一起下飞机。
尼克松事先就精心安排了这一公开露面的时间。因为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而此时正是美国的晚上10点30分,是美国的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
周恩来见尼克松和夫人步出机舱,面无表情地等候在舷梯边,当尼克松走到舷梯的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欢迎。
尼克松步下舷梯时,并未看到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也没有轰鸣的礼炮,机场也未铺设红地毯。看到周恩来,尼克松按照中国习惯鼓着掌,微笑着首先向周恩来郑重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周恩来也伸出了手,二人用力紧紧地握着,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1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在事后这样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中外记者在这个非常时刻,拍摄下了一张又一张富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照片。可是尼克松一松手,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标语——“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这时,尼克松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在短暂的寒暄后,尼克松又看到了他生平从未见过的最大规模的仪仗队。照惯例,在外国元首首次来华访问时,仪仗队由120人到155人组成,但这一次出现了中国外交史上规模空前仪仗队伍,共有371人。
由于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确定的接待尼克松的方针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因此只安排了在机场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也不搞群众欢迎。
中国仪仗队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中国仪仗队是我所见最为出色的,这些士兵高大、健壮,穿着笔挺,人数众多,动作整齐划一。”
在场的中外记者将摄像头对准了仪仗队,他们用镜头记录下的,还有美国总统身后不远处立着一人多高的标语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
当军乐队奏响两国国歌时,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尔后,两人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牌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
在从机场去往北京市区的途中,尼克松并没有看到欢迎的人群,而是看到了大街小巷墙上刷的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这和机场的标语牌如出一辙。尼克松在闻讯翻译得知标语的含义后,脸上略带苦笑。
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尼克松一行。他向尼克松介绍傅作义说:
“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立了大功。”
周恩来将章士钊先生晚年修订的《柳文指要》一书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作纪念。周恩来还专门向尼克松介绍了章士钊先生的情况;他还说,这部书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柳文指要》的书稿在1965年刚送到中华书局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出版一事自然被搁置起来。1970年,毛泽东问及出版《柳文指要》的事,章士钊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他写道:“夫唯物主义无它,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3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彼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毛泽东深知章士钊的秉性和为人,看了他的来信,立即指示有关方面将书稿发排出版。就这样,《柳文指要》一书终于在1971年9月正式出版,共14册。
周恩来在午餐结束后,对基辛格说:
“总统和博士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
基辛格闻言甚喜,没有料到中方会安排得这样快。这使他很兴奋,问道:
“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做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并说:
“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快一点行吗?”
尼克松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此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不时地询问尼克松到京后的情况。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为他画了鞋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色布鞋。
医务人员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还在尽可能接近会见大厅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
据吴旭君回忆说:“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要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感人。”
2月21日下午2点40分,尼克松、基辛格和随员洛德,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步入了毛泽东的书房。为了把这次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
基辛格这样描绘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型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
基辛格所描绘的沙发,是一个半土半洋、土洋合一的沙发。原来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多半是俄式的,既大又高,毛泽东常常感叹:“做沙发的人也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得多,只考虑高的人。”的确,像毛泽东身高1.83米的人,晚年也不适合坐这种高大的沙发了。他常常几天睡不好觉,吃两次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在沙发上也有些坐不稳了,因为无法把握自己的重心,身子常不由自主地往下滑。毛泽东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卫士、护士、保健医生都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他们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要求为毛泽东重新做一个沙发。很快,中央警卫团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到北京南郊木材厂,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沙发:高度为1米,长0.7米,宽0.9米,基本适合老年人坐。为了装饰,沙发底座蒙上赭红毛料布面,木腿架上刷了漆,外套米黄色和绿黄相间的草席,虽显得土气,却也实用。毛泽东坐在这个沙发上,发现身体不再下滑,他摇了摇身躯,高兴地说:
“这种沙发好多了。”得到了一个合意的沙发,他立刻想到了周恩来,就说:“总理个子比我矮,坐那种俄式大沙发,会更不舒服,因为除了身子下滑,腿还悬着,坐久了会发麻。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不久,周恩来就也有了一个与毛泽东一样的沙发。
欲知毛泽东和美国客人会谈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72年2月5日,周恩来将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于1月22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批示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进口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成套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为建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从发达国家进口新技术成套设备的一个极为常见的实例(请参看本传在后边多处章节中列举的引进外国成套技术设备的例子,特别是在第23章中提到的1973年3月的“四三”方案,引进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成套技术设备最后多达51.4亿美元)!让那些睁着眼睛散布“闭关锁国”论的人们,闭上他们的臭嘴吧!